#黎朵
Text


可以跟你交換一口嗎?【日安同學漫畫】
多謝款待!(一語雙關)
角色/ #黎朵 #席波
#原創#漫畫#日常#百合#可愛#女孩#席波#黎朵#吃飯#日安同學#rihantongsyue#comics#manga#drawing#台灣#taiwan#搞笑#yuri manga#yuri#original manga#goodayclassmate#lovely#glassesgirl#sportgirl
12 notes
·
View notes
Text
#video#video tumblr#video douyin#video animation#song#我错把黑夜当黎明#singer#欧阳朵#ou yang duo#movie#entergalactic#thoughts#choices#problems#love#sadness#rain
4 notes
·
View notes
Text

黎深用最后的力量将即将凋零的茉莉花瓣重新整合成一朵完整的茉莉花用冰封存
9 notes
·
View notes
Photo

【Takarazuka・Flower Troupe】Yuzuka Rei The set of the “Double-headed Eagle”, the dance ball...an assembly of glamorous beauty. The stage set in the politically unstable 19th century Austria, it portrays the story of the joy and struggle of finding true love
【寶塚・花組】柚香光 以「雙頭鷹」為舞台的舞會⋯集結了美輪美奐的美感。舞台設置在政局動蕩的19世紀奧地利,描繪了尋找真愛的快樂與掙扎
(Original article from Fujin Koron 原文來自婦人公論)
The set of the “Double-headed Eagle”, the dance ball and the numerous military uniforms and dress – all of this is an assembly of glamorous beauty. This famous work by Shibata Yukihiro was performed again and again, and this time it would be revived in the Grand Theatre after 30 years under the adaptation and direction of Koyanagi Naoko. Yuzuka delivers the joy and struggle of finding true love. It is refreshing to see how the tragic love story of Rudolf and Marie was approched as a human drama in the politically unstable 19th century Austria.
「雙頭鷹」的佈景、舞會和眾多的軍服、長裙——這一切都是美輪美奐的集結。在小柳奈穂子的潤色和執導下,時隔 30 年後在大劇院再演。柚香光傳達了尋找真愛的喜悅和掙扎。看到魯道夫與瑪麗的悲戀在如何政治動蕩的 19 世紀奧地利燃起愛火是富有新鮮感的。
The dignity of the Habsburgs and how dangerous it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blonde hair, and other matters such as the military uniform, Yuzuka Rei plays the role of Rudolf, the Crown Prince of the Austra-Hungarian empire.
While associated with the dignity of the Habsburgs, he also faced the danger of being confined to positional restrictions.
Upon a fateful encounter, he met Marie whom he looks at her with gentle eyes, calling her “a little blue flower”.
哈布斯堡王朝的尊嚴與危險
與金發、軍服等相得益彰的是,柚香光飾演的奧匈帝國皇太子魯道夫一角。
在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尊嚴聯繫在一起的同時,他也面臨著被局限於皇太子位置所限制的危險。
一次宿命的邂逅,他遇見了瑪麗,他用溫柔的目光看著她,稱她為「一朵藍小花」。
◆ Summary of “MAYERLING” 「梅耶林」概要
In 19th century Vienna, Crown Prince Rudolf (Yuzuka) spent his every day bound by a political marriage without love and his affairs, aspiring to lead a free life just like his cousins such as Johann Salvator (Minami Maito). One day, Rudolf fell in love with the pure baroness’ daughter Marie Vetsera (Hoshikaze Madoka). Unaware of the looming political conspiracies, they often met up again and again...
19世紀的維也納,皇太子魯道夫(柚香)的每一天都被沒有愛情的政治婚姻和事務所束縛,憧憬要過著像他的表兄弟約翰 · 薩爾瓦多(麻衣美奈美飾)一樣的自由生活。有一天,魯道夫愛上了純潔的男爵夫人的女兒瑪麗 · 韋瑟拉(星風まどか),不覺政治陰謀在即,兩人屢屢相見⋯

Minami plays as Johann Salvator. Taking the role of a storyteller, she plays a man who celebrates freedom, showcasing kindness and masculinity naturally.
水美飾演約翰 · 薩爾瓦多。如同故事的旁白,她很自然地飾演一位善良、呈現男性魅力,高呼自由的男人。

Towaki Sea plays as the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whose role was more deepened in this rendition. Her acting radiates the reflection of passing of time in light and shadow.
永久輝せあ飾演法蘭茲・斐迪南大公,隨著再演變得再給深化的角色。從她的演技,反映著時光的光與影。

It was impressive to see that Marie is not only cute, but also shows a sense of motherhood and Rudolf almost seem like finding her for salvation.
看到瑪麗不但可愛,也有母性的一面,魯道夫更要向她尋求救贖,是很深刻印象的。
Takarazuka Spectacular “ENCHANTEMENT–Luxurious Perfume–” 「–ENCHANTEMENT–華麗的香水」
This is a revue delivered by Noguchi Kousaku which is inspired by the “ka” (香 = scent) from Yuzuka Rei’s name.
It’s a beauty and glorious performance delivering the sweet and fragrant scent to the audience.
Not only is there the forest in Paris, but also the NY streets and a night club where the gentlemen are assembled.
It is exploding with the various colours and charms of this stylish Flower Troupe.
It looks like a hot dance battle in the night club where the men are wearing unique suits. It is heart-fluttering to se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oukis Minami and Yuzuka.
這是野口幸作的一個レビュー,靈感來自於柚香光名字中的「香」。
這是一場美麗而輝煌的表演,為觀眾帶來甜美芬芳的香氣。
不僅有巴黎的森林,還有紐約的街道和紳士云集的夜總會。
時尚花組爆發著各種色彩和魅力。
男人們穿著獨特的西裝,就像是在夜總會裡進行一場火熱的熱舞大戰,看得見同期水美和柚香之間的聯繫,讓人怦然心動。

#yuzuka rei#hoshikaze madoka#minami maito#towaki sea#柚香光#星風まどか#水美舞斗#永久輝せあ#花組#flower troupe#takarazuka#hibiscustranslation
37 notes
·
View notes
Text
here's an izzy/ofc fanfic that i concentrate most of my feelings towards him…dont have time to translate anything so duuhhh hope you guys enjoy
亲爱的Izzy,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想必你不关心。昨天我在洛杉矶郊区的一棵椰树下遇见你,你没有认出我来,只是从我的右边擦过去了。“请让一下,女士,”你这样说,声音和几年前差不多,却比几十年前哑了,我站在原地为你侧身让路,眼泪却滴下来了。Izzy,我从未想过让你记住我,那一刻却在晃神中有些动摇了,Izzy,我想,也许我根本就不爱你,也许我现在才开始爱你——Izzy,我都不在乎了。
1979年我在拉法叶遇见你,你苍白而年轻,双眼闪着光。你躺在后山的草坡上分给我一包塑料包装的白粉,教我吸入,再在我闭眼的时候吻我的嘴唇,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吻。我告诉你你应该当一个摇滚明星,你说你会弹吉他还会打鼓——那是我迷恋地摩挲你指尖的琴茧。我也许一辈子都出不来,也许明天就会成为全美最拉风的摇滚明星,你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当时认真觉得你会和我结婚,我们一起在洛杉矶住大房子,去欧洲巡演再在巴黎偷偷溜走看傍晚的灯火,Izzy,我当时认真觉得我们会有未来。
晚上你会翻我的窗户——夏天你手上出的汗加大了攀爬的难度,等到翻进我房间的时候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事实证明没有。绸缎系在我的发间,是你用手穿过发丝绑上的。我父亲管的很严,我怕他听见,一整晚在你身下我几乎不敢呻吟出声,眼泪从脸颊两侧流下,比往常多三四倍的眼泪从两侧流进枕头,我意识到你也许从来就不会属于我。
高潮的时候我轻声叫你的名字,你那时还叫Jeff,我却脱口而出Izzy——语音落下的那一刻我不敢去看你的眼睛。我记得你的眼睛,那双榛子色的,忧郁迷离的眼睛,自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所期盼的爱。只是十六岁太过年轻而我太过幼稚,我以为,我以为——可就连第二天早上醒来的床边都没有你。你离开了,你再没有回来过。
1987年我在纽约开一家唱片店,进货的时候看见一张新唱片,翻过来一瞬间对上的却是你的眼睛——我却不惊讶。打开唱片机我又听到你的歌,那一瞬间我知道你成功了,你站在洛杉矶的丛林顶端,我却想,你一定有很多新的情人吧。我想对我的朋友说那个Izzy Stradlin是我曾经的爱人,但我们只有过24小时的爱情,你走了,你永远走了,我也并不希求你回来。Izzy是我的一个梦,现在他是很多人的梦了。
第二次见你,你在我的城市开演唱会,我请朋友买了第一排的票,就只是看着你。你邀请我到后台去,我想我大约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了。化妆间还是卡车,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都有。那次你和乐队带着我从纽约到芝加哥一路狂欢,你抱着我蜷缩在后座,那一刻我以为你还记得我,却听到你的队友议论说这次的女孩没有上次欢快了。我一愣神,手上的香槟酒洒在了裸露的大腿上,粘腻地顺着腿流下,你仍然抱着我,用和8年前一样的双手拭去我的眼泪,你是我见过的女孩里最容易流泪的,你说,眼睛聚焦于我涂成鲜红色的嘴唇,却吻我的双眼,别哭,你说,别哭。是啊,Izzy,我的双眼永远含着泪水,Izzy,这么远的距离,我怎么可能不哭泣?
我仍然记得你是如何抚摸我的:从脖颈再到双乳,向下直抵腿心,你的双手带有一层薄茧,左手的指尖发硬,划过皮肤时我一阵战栗强忍着才能不流下眼泪,而长期的记忆与依恋使我几乎是在你的手触及我大腿内侧的那一刻便高潮了,你看着我,像是看一朵易碎而新奇的玫瑰。当晚跨坐在你的腰间我崩溃得无声无息,你只当我是爽了,便又往里顶了一下,眼泪就泉涌一般和下身的水一起淌下了。我知道第二天清晨你就会走,也许不会,但你总要离开的,我却也不死心,也许,也许你会爱我���?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皮肤上好吗Izzy,我开口问,递给你一把小刀。你没有反对,只是低下头,片刻以后你的手臂内侧出现了一个鲜红的血淋淋的名字,晃得我愈发清醒。疼吗,我问你,你摇头,我就往我自己大腿的内侧一样刻了你的名字,同样鲜血淋漓,同样醒目。现在这道疤还在我的腿上,你的呢,Izzy?你还记得这道痕迹吗?你会想到我吗?我没有机会再看了,如果有,我也只会记得去吻你的嘴唇吧。
后来我搬到洛杉矶,常常在唱片店和酒吧看见你的我却从未和你打过招呼。你有一次认出我来——也许没有认出来,你请我喝一杯,半夜我们在洛杉矶城郊的酒吧里互诉衷肠。你说你从来就不想做摇滚明星,只是年轻时有个女孩告诉他他应该去,脑子一热竟真的开始努力搞乐队,现在想想这简直是他人生的分叉口。我多想说Izzy,你看看我,那就是我呀,我就是那个女孩,你后悔吗?我们一起逃走好不好,Izzy,Izzy,我们一起逃走好不好?当晚我喝的烂醉,以至于在你吻我的那一瞬间我再一次地顺了上去,我也许真的爱你,Izzy,在同一时刻我能感受到我的眼泪顺着双颊流下来了,流进大敞着的领口,流下我的躯体,直到下一滴眼泪续上它的轨迹。别哭,你又一次说,我却将脸别过了。
而当我在那棵树下见到你时我并不意外。我生病了,长年累月的贫困使任何的病痛对我都如同灭顶之灾,难以应对。我深知时日无多,却不知我剩下的岁月该如何蹉跎。我想也许我爱你——也许我只是需要一个晚上而非三个,然后用一辈子来怀念那一晚的每个细节。三晚太长,我甚至很难回忆起你身上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Izzy?我与你擦肩而过时闻到的仍然是烟味,而第二次你的身上多了一种酒精挥发后的刺激性气味,像威士忌,再混合一些大麻和香烟的味道弥漫开来,你仿佛又在我身上了。我闭上眼,Izzy,医院走廊的酒精味不像你,而我又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你呢?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吧,成百上千个情人,成百上千个晚上,我想对你来说记住一个人比我更难。也许明天你就会忘了我,也许你根本没读到这里,我只是想,也许我需要告诉你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有个人正燃烧着她的灵魂爱你,爱得仿若顷刻之间便要灰飞烟灭一般。我爱你,也许这是早已难以改变难以逃脱的事实。长长的三晚,短短的三晚,我有时候想也许你会记住我至少一个细节。我是多想让你记住我啊!
直到那一天,我自你的身边擦过,恰恰带起了你的衣袖:我看到你手臂内侧根本就没有疤,我的大脑轰地一声炸开了,也许你我根本就是陌生人,明天早上醒来,我就会死了。长久的睡眠中你会带我逃走吗?Izzy,这是一个深陷爱的泥沼中的女人绝望的呼喊,痛苦和爱一并高呼着,我听不见,我的双眼模糊了。你怎么会说你不是摇滚明星呢?你明明是天生的摇滚明星,仰慕和爱和一切的目光,恨,摇滚明星的身上永远聚焦着一切的一切,而我是你一夜情后抛弃于觥筹交错之间的年轻荡妇,你明亮的生命里灰暗的角落,但是Izzy——我觉得你不会读到这里的,事实上,你根本不会读这封信——我又喝了一杯苦艾酒。也许我该假装我们已经到了巴黎。
你真诚而绝望的,
Izzy早上醒来在信箱里发现一封发黄的信,落款空着,收信人写着他的名字,他打开了,读了两行便扔在了一旁,在他身后的秋风里,玫瑰暗红色的花瓣落了一地,血流如河。


#izzy stradlin#groupie love#izzy stradlin/original female character#izzy stradlin/reader#fanfic#guns n roses#i love him so much how#hes the love of my life#fucknleavelit#neverloved
2 notes
·
View notes
Text
2023 Reading Log
In order of completion...



(Audiodrama art for The Plays of Lips and Teeth, Concealed and Blended: Fendai, Joyful Reunion)
1. 唇齿之戏 张佩奇 -- The Plays of Lips and Teeth [#cczx]
2. 粉黛 七世有幸 -- Concealed and Blended: Fendai [#fendai]
3. 天潢贵胄 漫漫何其多
4. 我成了虐文女主她亲哥 刘狗花 -- I Became the Older Brother of the Heroine in an Abusive Novel [#nwnz]
5. 相见欢 非天夜翔 -- Joyful Reunion [#xjh]
6. 陛下万安 决绝 -- Your Majesty, Be at Ease [#bxwa]
7. 总裁的狮子驯养日记 患者阿离
8. 妃嫔媵嫱 七月侯 -- Fei Ping Ying Qiang [#fpyq]
9. 铜雀春深 北有乔木St
10. 不枉 余酲
11. 天官赐福 墨香铜臭 -- Heaven Official's Blessing [#tgcf]
12. 魔尊他念念不忘 墨西柯 -- The Demon Venerable’s Wistful Desire [#魔尊他念念不忘]
13. 书穿后被暴君标记了 池翎
14. 督主有病 杨溯 -- Governor’s Illness [#dzyb]
15. 日落大道 卡比丘 -- Sunset Boulevard [#sunsetblvd]
16. 火焰戎装 水千丞 – Blazing Armor [#hyrz]
17. 内娱第一花瓶 三三娘 [#dyhp]
18. 邪门的爱情出现了 丧心病狂的瓜皮 -- Evil Love Appears [#邪门的爱情出现了]
19. 花瓶 困倚危楼 -- Flower Vase [#花瓶 困倚危楼]
20. 太平长安 盐盐Yany -- Placid Chang’an [#tpca]



(Mao'er audiodrama cover for I Became the Older Brother of the Heroine in an Abusive Novel, and Governor’s Illness , and Ximalaya audiobook cover for Blazing Armor)
21. 恰如其分 菡萏花开
22. 逢狼时刻 吕天逸 -- Meeting the Wolf
23. 亡命之徒的退休生涯 FOX -- The Retirement Life of a Runaway Desperado [#wmzt]
24. 望春冰 符黎
25. 凛冬岑寂 长不出青苔
26. 荒野植被 麦香鸡呢 -- Wilderness Vegetation [#hyzb]
27. 作践 十步方寒 [#作践]
28. 可一可再 反舌鸟 [#可一可再]
29. 隐婚 久陆
30. 残疾战神嫁我为妾后 刘狗花 -- After the Disabled God of War Became My Concubine [#cjzs]
31. 楚囚 林萨
32. 贪恋 莫以风 (original AD)
33. 富贵长安 五朵云 -- The Rich And Honorable Chang'an
34. 交易沦陷 在下小神j [#交易沦陷]
35. 臣服 墨奈何/墨青城 -- Surrender (Book 1) [#臣服]
36. 臣服II 墨奈何/墨青城 -- Surrender (Book 2) [#臣服2]
37. [重生]昨年 素飞柳
38. 每天都想抱崽的Omega 杳杳一言
39. 苏长清倒霉的一生 月色霜华
40. 渠清如许 清明谷雨



(audiobook cover art for Wilderness Vegetation, AD cover art for 作践, After the Disabled God of War Became My Concubine)
41. 泾渭情殇 请君莫笑 (GL) -- Clear and Muddy Loss of Love [#jwqs]
42. 然后就爱了 viburnum
43. 九千岁[重生] 绣生 [#九千岁]
44. 游龙随月 耳雅 [#ylsy]
45. 小福晋 半缘修道 [#小福晋]
46. 三嫁咸鱼 比卡比 -- Married Thrice to Salted Fish [#sjxy]
47. 合意 楚寒衣青 [#合意]
48. 陛下有一段白月光 天北闻秋 [#陛下有一段白月光]
49. 暗河长明 冷山就木
50. 欲言难止 麦香鸡呢 -- Eternities Still Unsaid Till You Love Me [#欲言难止]
51. 老婆是顶级Alpha,我该怎么办 海藻大王 [#老婆是顶级Alpha]
52. 有名 木更木更 -- In Name Only [#有名]
53. 心毒 初禾 -- Poison of the Heart [#心毒]
54. 危险人格 木瓜黄 -- Dangerous Personality
55. 穿成苏培盛了 一渡清河 [#ccspsl]
56. 为什么这种A也能有O 图南鲸 -- Why Is It Possible For This Type Of A To Also Have An O? [#为什么这种A也能有O]
57. 寒武再临 水千丞 -- The Return of Cambrian Period [#hwzl]
58. 奉君侧之十年心 天娜
59. 奉君侧之生死劫 天娜
60. 龙血/养父 水千丞 -- Dragon Blood



(Mao'er audiodrama cover for Clear and Muddy Loss of Love, In Name Only, and Dragon Blood)
btw ... I feel obligated to disclaim that just because I finished a novel doesn't mean I don't regret it or would recommend it ...
Books which I have read significant amount but stopped (but think I would like to finish someday ... )
剑名不奈何 淮上 -- The Sword Named No Way Out
电竞魔王集结营 青梅酱 -- The E-Sports Circle’s Toxic Assembly Camp
长安少年游 明月倾 --
德萨罗人鱼 深海先生 -- Desharow Merman [#德萨罗人鱼]
余污 肉包不吃肉 – Remnants of Filth
忧郁先生想过平静生活 青色羽翼 -- Mr. Melancholy Wants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yyxs]
魔尊也想知道 青色羽翼 -- Devil Venerable Also Wants to Know
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 骑鲸南去 -- Don’t Pick Up Boyfriends From the Trash Bin
情敌每天都在变美 公子于歌 -- Your Rival in Love Gets Prettier Every Day
燎原 不问三九 -- Wildfire
沉舟 楚寒衣青
楚天以南 大风不是木偶 -- Under Clear Skies
乱世为王 顾雪柔/非天夜翔 -- To Rule in a Turbulent World
人鱼陷落 麟潜 -- The Fallen Merman
谁把谁当真 水千丞 -- Winner Takes All
凤于九天 风弄 -- Feng Yu Jiu Tian
营养过良 芥菜糊糊 -- The Nutrition is Too Good
Tags for works I haven't started reading:
六爻 Priest -- Liu Yao: The Revitalization of Fuyao Sect [#liu yao]
台风眼 潭石-- The Eye of the Storm [#tfy]
判官 木苏里 -- Panguan [#panguan]
9 notes
·
View notes
Text
皮埃罗:你为何如此忧伤
皮埃罗:你为何如此忧伤? 玛丽安:因为你用诗句(words)对我说话,我却含情脉脉看着你。 皮埃罗:与你交流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观点,只有感情。 玛丽安:不!感情饱含了观点(ideas)! 皮埃罗:好…让我们严肃点谈,告诉我你所喜欢的,你所想的…我也会告诉你。好的,你先。 玛丽安:花、动物、蓝色天空、音乐的喧闹,我不知道…一切!你呢? 皮埃罗:野心(Ambition)、希望(hope)、事物的运动、事故/意外,呃…还有呢…好的,一切! 玛丽安:知道吗?5年前我是对的,我们永远不能互相理解。 玛丽安:这是事实,你知道。 皮埃罗:我信你,骗子。 玛丽安:为何不信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用我自己的方式。 皮埃罗:真的? 玛丽安:我能证明。看…我回去了海滩拿你的日记本。 皮埃罗:弗兰克有钥匙? 玛丽安:我完全能解释。 皮埃罗:你有恋人? 玛丽安:我完全能解释。 皮埃罗:他吻过你吗? 玛丽安:我完全能解释。 皮埃罗:我紧紧抱着她开始大哭。 玛丽安:这是我们第一个和唯一的梦。 玛丽安:又是我们的了。 皮埃罗:什么? 玛丽安:永恒。 皮埃罗:不,那只是大海。 玛丽安:还有太阳。 皮埃罗:同从前一样神秘,我明白。 玛丽安:不,我只是不想谈自己。 皮埃罗:好,别说了。 收音机:…驻军被越共屠杀了…越共死伤115人。 玛丽安:可怕,不是吗?无声无息… 皮埃罗:什么? 玛丽安:他们说“115名游击队”。对我们什么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人,即使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他妻子,他是否有孩子,他是否喜欢看电影或玩。我们一无所知,他们只说了115人被杀。就像照片,常令我们着迷。你看见一个下面有标题的人的快照,他是懦夫或好人,但在拍照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妻子?还是他的情妇?是过去?未来?还是一场篮球赛?没人知道。 皮埃罗:这是你的生活。 玛丽安:对…正是这令我悲伤——书与生活如此不同。我希望它们是一样的——清楚,符合逻辑,有组织…但不是。 皮埃罗:对,超乎人的想象。 玛丽安:不,不是,皮埃罗。 皮埃罗:我的名字是费迪南…我不想再说一次! 玛丽安:我知道…但你不能说——我朋友费迪南。 皮埃罗:如果你想,你可以,玛丽安。 玛丽安:我想。我愿意做你想的一切。 皮埃罗:我也是,玛丽安。 玛丽安:我把手放在你膝盖上。 皮埃罗:我也是,玛丽安。 玛丽安:我要吻遍你全身。 皮埃罗:我也是,玛丽安。 皮埃罗:你父母还活着吗? 玛丽安:当然,他们从没分开过。有一次他们差点分开,爸爸要去旅行„,不是出远门,他们没钱买两张票…妈妈和他去了车站…他们互相张望,爸爸在里面,妈妈在人行道,汽车启动时爸爸匆忙下车,他不想离开妈妈,他在前面下车时她在后面上车,因为她不想离开他,最后爸爸放弃了旅行。 皮埃罗:你在商店干什么? 玛丽安:看人们的脸。……为何问这些问题? 皮埃罗:我想知道你是谁,即使5年前我也不认识你。 玛丽安:我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你真是一个傻瓜,令这些变得如此神秘。听我说,一小时有3600秒,这使得一天有100000秒,一辈子有…2500亿秒,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月,加起来,你会发现我和你在一起只有几百万秒的时间…只是2500亿秒中的一滴,并不算多,所以我不认识你是谁,并不奇怪。 皮埃罗:明白吗?我是对的。 玛丽安:关于什么? 皮埃罗:你不相信我们会永远相爱。 玛丽安:不。我从没告诉你我会永远爱你。(唱:“亲爱的,你从没发誓你会永远爱我。我们从没这样发誓,你知,我知。我们从没想过会被爱吸引,由于我们薄情寡义。至今渐渐的,我们没有话说,一点一点的。感觉在我们快乐的相合的身体上流逝,爱的语言在我们赤裸的唇上复活,一点一点的。大量爱的语言开始相合,温柔的,伴着我们的吻。有多少爱的语言?我从没想过我一直需要你,哦,我爱��。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两个能够永远不厌倦的生活在一起。每天早上起来充满新奇和欢乐,在同一张床上,除了这种简单的快乐,这种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别无其他欲求。至今渐渐的,我们没有话说,一点一点的。感觉无所顾忌的把我们紧缚在一起,直至永远。感觉强过任何爱的语言。已知或未知,感觉如此的狂野和强烈,我们从未想过的感觉,过去是可能的,不是曾经许诺过一辈子爱我吗,让我们不要再做那样承诺了,你知,我知。让我们保持这种感觉,我们的这份爱。我们的这份爱,将短暂而甜蜜。”) 皮埃罗:临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时是60年后,我们将知道我们是否永远相爱。 玛丽安:不,我知道我爱你。但我不知道你。 皮埃罗:我也爱你,玛丽安,我爱你。 玛丽安: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皮埃罗:总的来说。 玛丽安:这是一部冒险电影。 皮埃罗:《血染的项链》。 玛丽安:总的来说。 皮埃罗:《月色温柔》。 玛丽安:一个爱情故事。 皮埃罗:一个爱情故事。 玛丽安:《月色温柔》。 皮埃罗:一个爱情故事。 皮埃罗:第八章。 玛丽安:地狱一季。 皮埃罗:第八章。 玛丽安:我们穿过法国。 皮埃罗:就像阴影。 玛丽安:穿过镜子。 皮埃罗:我们看到梵高决定剁掉自己耳朵的咖啡馆。 玛丽安:你是骗子,你看到什么? 皮埃罗:我看到… 玛丽安:他还在写日记 皮埃罗:因为写作可以驱散 玛丽安:环绕在它周围的阴影 皮埃罗:即使它在明天的生活中淡化了 玛丽安:文章留下的只是纯粹的东西 皮埃罗:第八章。 玛丽安:地狱一季。 皮埃罗:爱需要重复创造。 玛丽安:真正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无数个世纪过去了,就像许多风暴。 皮埃罗:我抱紧她,开始哭泣。 玛丽安: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和我们唯一的梦。 皮埃罗:你来吗? 玛丽安:去哪儿? 皮埃罗:去神秘岛。就像船长格兰特的孩子。 玛丽安:去干什么? 皮埃罗:没什么,只是放松。 玛丽安:似乎没趣。 皮埃罗:这是生活。 皮埃罗:我不喜欢菠菜(胡说八道)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喜欢,我就会吃掉它。我不能忍受废话。和你一样,只有一条路。有一部影片,里面迈克尔西蒙被这个女孩带走… 玛丽安:你又想重新来过! 皮埃罗:我并非有意如此恶心。 玛丽安:你说我们能坚持到最后。 皮埃罗:对…到黎明。 玛丽安:第七章。 皮埃罗:以为叫佐伦(revolver)的诗人。 玛丽安:罗伯特·布朗宁。 皮埃罗:逃走。 玛丽安:从不。 皮埃罗:心爱的人。 玛丽安:只要我是我自己。 皮埃罗:你是你。 玛丽安:只要宇宙会容纳我们。 皮埃罗:我,爱你。 玛丽安:你,拒绝我。 皮埃罗:只要我们想逃(run)。 玛丽安:多么像命中注定。 我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谈话,但它们似乎不是统一体,没有一致。人应感到同一,我觉得自己被分得支离破碎。 一个人的时候说话会很多。 或许我在白日做梦 她令我想起… 音乐 她的脸… 我们已经到了… 中年 我们不再需要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当玛丽安小姐说:很好的一天 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只能想象她说:“很好的一天。” 其他没什么 为何要描画得一清二楚? 我们是由梦组成,梦是由我们组成 今天天气很好,亲爱的 无论在梦中,在语言中,还是在死亡里 今天天气很好,亲爱的 今天天气很好 在生命中 我听说在河对面有一个舞厅,我要去跳舞。如果我们被人杀了,就太糟了。他们会赶上我们…又怎样?星期二,我想买一台电唱机,但是他把所有的钱用来买了书。事实上,我没有理会。但他始终执迷不悟。我不睬书…还有碟,也不喜欢钱。我只想生活。但他永远不明白。 我希望时间可以停止不动。看,我把手放在你腿上,很美好。这是生活。空间…感觉…相反,我跟你走…回到我们的愤怒的吵架故事中,我不在乎。 费迪南给他们讲盖尼蒙的故事,但他们不听,然后他说起夏天,还有渴求温暖夜晚空气的情人,他谈起人类,季节,还有不期而遇的遭遇,但他告诉他们不要问先有什么,和万物的语言…还有接下来是什么,我感觉自己活着,这是关键。 任何造物,面对自然,都会相信。 眼睛:人类的风景画… 嘴:用语言来拟声 堕落产生诗的语言 作家呼吁其他人的自由 诗是失败者的游戏 实际上 唯一有兴趣的是 人们走的路 悲剧是一旦他们明白… 他们要去哪儿和他们是谁 其他一切仍是个谜 简而言之 永远不解的谜是生命 过了五十岁,维拉斯克停止画确定之物。他盘旋在物体周围,随同空气、晨曦,和他的影子,在空虚的背景中,看到色彩的心悸。它们构成了他的寂静的交响乐的无形核心。因此,他捕获的只是形状与声音的神秘渗透,构成一个持续的秘密的进程,不被任何喧嚣背叛和打断。空间的统治至高无上,就像天线波掠过水面,吸收有形的波并对他们进行定义和模式化,然后像香水一样散发出来,发出自身的回声,撒出一种无形的尘。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悲哀:一个堕落的国王,病态王子们,白痴,侏儒,残废。一群滑稽的畸形人装扮成王子的模样,他们的功能就是嘲笑自己和取消脱离法律约束的演员,在礼节、阴谋和谎言的罗网中被忏悔和自责所缚,伴随着门边的审讯和沉默。乡愁遍及他的作品,尽管他极力避免其中丑陋的一面,关于那些受到压抑的孩子的悲伤和恐怖。维拉斯克善于描绘开阔地区的和安静的傍晚,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下还是在关闭的屋子里面,即使耳边有战斗声和打猎声。因为这些很少在夜晚出现,当一切沐浴在热带的阳光之下,这位西班牙画家与夜晚私语。《狂人皮埃罗》
6 notes
·
View notes
Photo

🧋Ce Bubble Tea nous fait voyager à Hong Kong, un des meilleurs Bubble Tea de Paris, les gâteaux 🍰 ont un cœur asiatique, j'aime le gâteau Yuzu, sésame citron, roulé fraise et rhubarbe, 👍n’hésitez pas à commander aussi une boite de roulé Pork Floss Roll, c’est le meilleur que j’ai jamais goûté. @lordome_paris15e 👉L'ORDÔME 🧋Pâtisserie, Salon de thé 📍41 Rue Desnouettes 75015 Paris 👉这家的招牌奶茶让我喝到了国内第一杯丝袜奶茶的味道,每次都觉得好好喝! 生椰拿铁,豆花燕麦拿铁也不错,胖乎乎软绵绵的现烤肉松小贝像在吃云朵,大概是我吃过巴黎最好吃的小贝吧! yuzu伯爵茶一如既往好吃,质量超高的日式中式法式融合甜品店,巴黎真的越来越多好吃可以媲美法甜的国人开的甜品店👏🏻 ~ #dessert #desserttable #dessertlover #desserttime #dessertpic #dessertparis #dessertgram #dessertlovers #dessertsofinstagram #dessert🍰 #dessertporn #bubbletea #patisserie #甜品 #甜點 #美食 #美食推荐 #巴黎 #法国 ##parisfoodporn #parisfoodies #parisfood #parisfoodguide #foodbloggerparis #foodblogger https://www.instagram.com/p/CfYrUtDIoTK/?igshid=NGJjMDIxMWI=
#dessert#desserttable#dessertlover#desserttime#dessertpic#dessertparis#dessertgram#dessertlovers#dessertsofinstagram#dessert🍰#dessertporn#bubbletea#patisserie#甜品#甜點#美食#美食推荐#巴黎#法国#parisfoodporn#parisfoodies#parisfood#parisfoodguide#foodbloggerparis#foodblogger
4 notes
·
View notes
Text
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梦——评《春光乍泄》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李白《月下独酌》
有人说,如若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潜入海底,穿越地心,便到达了对香港而言的世界尽头——布宜诺斯艾利斯。而王家卫把故事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理由是:要让演员体会到一种绝望,并把绝望带进电影中。因为这“最远”的距离与绝望,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不会是意外。
《春光乍泄》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一对不被世俗认可的恋人,黎耀辉和何宝荣,从香港逃离到阿根廷,本来应该是春光明媚的生活,却在电影的开头蒙上了黑白滤镜。在共同经历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彼此失去信任的二人作别,黎耀辉回到了香港的家中,何宝荣却永远定格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租屋内。
“春光乍泄”的片名,猛一看便带有些许的香艳意味,影片中王家卫导演十分大胆地拍摄了许多亲密镜头。而“光”的意象,在影片中有多处体现:不论是黎耀辉为何宝荣做饭时,窗外泻下的一缕微光;还是黎耀辉在露台上工作时明媚的阳光;亦或是二人在厨房里翩翩起舞时的温暖的白炽光,“光”总是带给观众温暖的感觉。二人相处的美妙时光总是浓墨重彩的,仿佛只因拥有彼此,这个世界才带有色彩;而当两人分离时,一切便重归黑白。
《春光乍泄》的英文片名是“Happy Together”,正因两人是在一起happy的,终有一日,当两人不再一同快乐地挥霍时光,而是趋于平淡地同甘共苦,这部电影便不复存在。英文片名限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黎耀辉与何宝荣注定不可能一辈子只追逐共同拥有的快乐,最后二人的分道扬镳也使得曾经共同快乐的时光显得弥足珍贵。
故事的开头是何宝荣在地摊上买了一盏旧台灯(台灯是整部电影暗藏的线索),台灯上描绘的是壮丽的伊瓜苏大瀑布,二人便驱车前往,但在途中迷路,在灰蒙蒙的色调中,二人争吵不断,最后何宝荣撂下一句“不如分开一下”便转身离开。影片开头中,黎耀辉十分无奈地说了一句“不如从头开始,这是何宝荣的口头禅”,在一幕中,黎耀辉捂脸时的无助与痛苦将内心的情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因为他的付出与迁就换来的只有何宝荣一次次没有理由的离开,这种痛苦又随着何宝荣不断回归与离开中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形成恶性循环。我想在这里,黎耀辉的耐心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本就是十分不易的,二人对香港的“逃离”后的甜蜜,似乎在一次次争吵与分离中消散殆尽。
何宝荣离开后,黎耀辉为了生计在酒吧打工,招揽生意,但是他遇到了和外国人在一起腻歪的何宝荣,本来嘴角带有一丝职业化微笑的黎耀辉周遭温度骤降,特别是在看到何宝荣与外国人激吻时,他只能站在门口。镜头转到何宝荣,他在车中点燃一支烟,脸上的狡黠好像预示着他料到黎耀辉一定会追上来,但是当过了几分钟他没有看到黎耀辉的踪迹时,他无力地瘫在座位上,脸上带着失望与落寞,进而转变为一种冷漠。在一分钟内完成“笃定自若与得意,再到局促不安、再到失望落寞,最终冷酷”的转变,张国荣的演技使我深深折服。
在与何宝荣重逢后,原本好脾气的黎耀辉却不再显得那么淡定,遇见吵闹的旅客也失去了为他们拍照的兴致,再次与何宝荣的见面,他只敢躲在酒吧里面,等何宝荣离开之后才敢出现。当何宝荣出现在黎耀辉家门口,两人扭打在一起,这个时候黎耀辉不再淡定,他的愤怒与嘶吼,不仅是对何宝荣放荡不羁的怨恨,更是对自己无法控制爱恨交加又嫉妒万分情感的懊恼。何宝荣的一句“我好想你陪我一下”却让黎耀辉夺门而逃,或许他害怕自己再次原谅何宝荣,开启另外一个恶性循环。
当何宝荣受伤后再度出现在黎耀辉家门口时,影片由黑白转为彩色。黎耀辉为他洗衣服、洗澡、做饭,两人似乎回到了快乐的时光。因为爱一个人,黎耀辉可以在感冒时为他炒饭、可以陪他去自己毫无兴趣的马场、可以爱上他的爱好——跳舞。两人共舞的这个片段是我在全片中最爱的场景。先前笨拙而认真学习跳舞的黎耀辉,镜头一转,在厨房中的二人翩翩起舞,温暖的黄色微光泻下,仿佛整个世界中只有彼此,二人笑意浓浓。这在一刻,什么舞步、音乐、节奏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彼此拥有,随后的深情一吻,或许是由于先前的分离,两人似乎都打开了心扉,倘若时间能够停滞在这一刻该有多好。
猜忌和怀疑往往是摧毁爱情的利器,张宛的出现使得二人中出现嫌隙,这个用耳朵感受世界的男人,因为自己的一个小玩笑,便摧毁了黎何二人本就如履薄冰的爱情。黎耀辉不知道何宝荣会因为自己不喜欢他在夜晚穿着光鲜而在家中等他,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争吵中的一句“我不是你”会给何宝荣带来多大的心理伤害,或许“我不是你”的下一句是“那么下贱”。而对何宝荣而言,与黎耀辉的争吵似乎是二人对感情的证明与发泄,明明已经伤痕累累却依旧要互相伤害,冷战磨去了他的耐心,终于在争夺护照中爆发,这时候的二人已经不信任彼此了,又一次扭打后,何宝荣离开了。
黎耀辉最终还是一个人前往伊瓜苏大瀑布,在瀑布的拍打中,他的脸上早已无法区分瀑布与泪水,而何宝荣也在黎耀辉的家中发现自己曾经买的台灯画的是两个人一起看瀑布的画面。黎耀辉在回香港前在台湾停留,此时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他在张宛家的店铺吃饭,最后拿了一张张宛的照片,张宛是他对的阿根廷之旅的纪念,而当他看到这张照片,就能想起那个他无法忘怀却也无法面对的身影。
如果说黎耀辉与何宝荣有什么共同点,我想是缺乏安全感与自卑。影片中,梁朝伟扮演的黎耀辉和我一直认知的梁朝伟并没有太多差别,他好像永远是沉默的,只有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才会露出情绪变化。在香港二人的爱情无法被接受,来到阿根廷好不容易和爱人团聚又害怕爱人不按常理地离去,当木讷的他偷偷藏起何宝荣的护照时,我想他的目的其实十分单纯,正是因为害怕失去,才会有一种想要把爱人拴在身旁的欲望。但是他忘记了一点,感情和流沙共通:越是想要握紧却流逝得越快。黎耀辉在香港有家,有父母,有工作,但是他为了和何宝荣在一起,选择离开家在外流浪。其实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家可回,至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等他回家。
张国荣扮演的何宝荣是一个既自卑又自负的形象,当他与黎耀辉扭打时,他问黎耀辉是否后悔和自己在一起,其实这个时候的他内心是十分没有底气的,在他人面前一贯嚣张的他却在黎耀辉面前显得十分卑微,当他最后一次回到黎耀辉的家中打扫时,好像是在等黎耀辉回家,但是他不会回来了。何宝荣没有家,所以他可以在外流浪,了无牵挂,那个曾经会等他回家的男人也离他而去,他是孑然一身的。何宝荣具有典型的表演型人格,他非常渴望能够得到黎耀辉全部的爱与包容,但却忘记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承受底线,而当他变得歇斯底里后,本就所剩无几的爱情便全部随风消逝,剩下的只有恨意与无奈,而这也是二人作别之时。
张宛这个角色的安排,在很多影迷看来是个败笔,甚至有人认为张宛这一角色使张震的形象显得不那么讨喜,但黎何二人失败的爱情真的就完全是张宛造成的吗?我想,张宛只不过是矛盾爆发的催化剂。黎何二人本身性格上就具有巨大的差异,黎耀辉沉默寡言,遇到问题并不会主动沟通,只是漠然在原地等何宝荣一次次的“回归”;何宝荣自负放肆,认为黎耀辉会永远在原地等他,却忘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这句至理名言放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张宛,还会有别人介入二人的感情中。张宛在一定程度上让黎耀辉清醒过来,他想将自己的遗憾与不快乐留在灯塔的愿望也促使黎耀辉独自前往大瀑布,黎耀辉最后选择同自己和解,他对何宝荣爱情的放手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解脱,他最后选择回到香港,回到家中,也是将张宛视作自己的“例子”。
有人说,王家卫没有给何宝荣一个结局,在我看来,这便是何宝荣最好的结局。他在影片的最后抱着黎耀辉的毯子放声痛哭,本就如同浮萍的他在这一刻真的失去了自己的归宿与依靠。他的生活很有可能是继续与男人厮混,继续放逐自我,继续流浪,但是他的心里却永远会有黎耀辉这样一个缺口。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无家可归,香港与布利诺斯艾利斯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不过都是流浪的“异乡人”。当画面定格在黎耀辉的那间出租屋内,这份淡淡心酸后的意犹未尽能够使观众有更多的联想。
《春光乍泄》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讲述同性的影片在很多地方如果换作是女性角色,一定会有不同的处理与理解,同性本就更为敏感脆弱的性格在影片中有几处体现得十分恰当。比如上文中提及的当黎耀辉看到何宝荣与外国人激吻时,如果何宝荣是女性,我相信黎耀辉或许会选择“冲冠一怒为红颜”,即使失败,至少也是一种雄性气概;如果是为一个滥交的男人争风吃醋,恐怕沦为他人的笑柄。另一处是当何宝荣执意要拿回他的护照时,男女在感情中扮演的更多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但对于同样具有征服感的何宝荣,他无法忍受被黎耀辉私藏在家中的行为,最后愤怒地离去。男人之间的愤怒往往会通过肢体冲突体现,在影片中,黎耀辉与何宝荣多次大打出手,二人的肢体动作虽然显示自己极度的愤怒,但落下的拳头却依然是相对轻柔的,或许这也体现出二人内心的不舍与无奈;对于异性而言,男女体格上的差异以及传统观念中“好男不和女斗”的思想使得男女之间遇到矛盾时更倾向于通过争论、吵架的方式来发泄。
近年来《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四个月亮》《爱在末路之境》等同性题材电影的热映体现出世界范围内对LGBT群体的高度关注,但是当我们回到1997年的香港,同性的题材还是十分前卫的。LGBT群体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爱情是不分性别、年龄(恋童癖除外)与种族的,正是由于世俗的偏见与来自不同方面的伤害,很多LGBT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在现今的中国,LGBT早已不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但是大众传媒却始终避讳提及LGBT群体的权利、生存现状与心理健康,甚至Bilibili在审核视频时不允许出现同性亲密镜头的片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对LGBT的歧视,而我们也同样需要努力推动社会的公平发展。
为什么整个社会对同性恋情具有如此大的恶意?首先在于,我们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的统治之下,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形成了“社会共识”,当男性想要跨越这样的社会共识进入“女性角色”时,他是会被男性群体歧视并抛弃的。其次,改革开放距今不过40余年,这些“非主流”的思想在很多人眼中是西方文化的糟粕,父母辈的思想开化程度自然是不如现代年轻人,同性恋的社会接受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社会学中性学与伦理学在中国依旧是较为新兴且先锋的学科,文化学在中国依旧是缺失的,社会普遍对酷儿理论理解程度不够,同时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发展的差异使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偏见。最后,部分同性恋者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将自己视作“弱势群体”,并以此获利,在互联网上发布仇恨言论(包括代孕问题、“同妻”问题以及仇女倾向),一些还并不具有成熟三观的青年逐渐两极分化,一部分无脑支持同性恋,另一部分逐渐“恐同”,这对同性恋群体是极大的伤害。
在我看来,爱情始终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生活在乌托邦中,周遭的环境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的一个同性恋朋友曾和我说,倘若世界能对他多一些善意,倘若他的父母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怪物并且强迫他去看心理医生,或许他会活的更开心一些。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他与我又有什么差别呢,倘若要以一个人的性向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正常”,这样的评判标准本就是极度不客观的,我们谁又是真正“正常”的呢?我想,如果不能理解,也请抱有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
缺乏安全感的爱情注定是不会长久的。世俗的眼光与流言蜚语都是杀人的利器,两个本就敏感的人活得小心翼翼,无法得到认可,只能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而当飘零至他乡,矛盾与冲突让本就伤痕累累的二人失去了信任感,爱情成为桎梏,有人想逃,有人却���留在原地。我想多年之后,当黎耀辉与何宝荣再度回想起布利诺斯艾利斯的那段曾经浓墨重彩、春光乍泄的经历,会不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恍惚:这一切都曾真实存在吗?
我想,布利诺斯艾利斯,不过是存活于春光中的一场梦罢了。
[1]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J].语丝,1926(47)
0 notes
Text
論一個面目猙獰的民族(45):
2024年3月28日,國土報社論:長期佔領加薩並建造定居點將構成戰爭罪和道德罪,只會加劇衝突,導致以色列遭到全世界的仇恨長期佔領加薩並建造定居點將構成戰爭罪和道德罪,只會加劇衝突,導致以色列遭到全世界的仇恨。
2024年3月28日,希法醫院倖存者: 人們被告知不要舉白旗,因為以色列人無論如何都會開槍 隨機處決,全家被屠殺並埋在瓦礫中,屍體堆積如山,惡臭難忍。
2024年3月28日,以色列士兵今天在他們的社交媒體帳戶上發布了這段視頻,顯示他們炸毀了加薩的一座清真寺。
2024年3月29日,短短3個月內就奪取了1萬多德南。佔領軍利用全世界都在關注#غزة戰爭的機會,奪取了西岸土地,並進行了30年來最大規模的奪取。
2024年3月29日,讓花朵變成沙漠:以色列消滅了加薩近一半的樹木和綠地 一場生態滅絕將加劇飢餓、野生動物的滅絕以及空氣和水的污染 精心策劃的策略,創造導致人口崩潰的條件;又稱種族滅絕。
2024年3月29日,以色列陸軍指揮官承認正在執行漢尼拔指令。 他們故意試圖殺害被俘虜的以色列人,因為“最好停止綁架”,而不是將以色列人活活留在哈馬斯手中。 哈馬斯希望人質活著。以色列希望他們死。
2024年3月29日,一名以色列士兵社群媒體帳號上的一段影片顯示,他們放火燒了希法醫院附近的數十棟巴勒斯坦房屋,然後拿這件事開玩笑。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病。
2024年3月30日,突發新聞:以色列剛在黎巴嫩南部用無人機襲擊了一輛載有兩名聯合國觀察員的汽車 聯合國觀察員被殺。
2024年3月30日,加薩戰爭強調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即大多數阿拉伯政權都是傀儡政權和政府,其主要功能是保護猶太復國主義者!
2024年3月30日,猶太復國主義拉比呼籲猶太人摧毀教堂…“我們必須淨化非猶太人”.
2024年3月30日,敏感影片片段:以色列空襲目標是阿克薩醫院的一個帳篷,裡面住著一些流離失所的平民和病人的護理人員。以色列的瘋狂、殘暴和野蠻超乎想像。戰犯與新記錄的戰爭罪.
2024年3月30日,突發新聞:據《國土報》報道,以色列在加薩設立了“滅絕區”,以色列佔領軍士兵被命令殺死任何會動的東西:平民、婦女、兒童、救援人員和醫務人員。
2024年3月31日,「北部仍然處於全面封鎖狀態,無法進入。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飢餓仍在繼續。」 -@FAO “我們現在收到以色列襲擊倉庫的報告。” -@UNOCHA “目前有數百輛卡車的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物資積壓。” -@UNICEF
2024年4月1日,這就是加沙希法醫院所剩無幾的地方。 此前,以色列否認轟炸醫院。西方國家對此給予了無罪推論。 現在,當它公開吹噓摧毀醫院時,西方卻保持沉默。 「疑罪從無」已經變成了共犯。
(加拿大司馬田2024.3. 谷歌翻譯fb:Markss Tang)
0 notes
Text
《第三黎明》 ver.1.4
前1,5000+字,放置了幾個月想重修所以期間限定公開供養
-
我第一眼見到他的時候,他開口第一句就先問我:「您弄丟這個了嗎,先生?」花了我數秒時間才反應過來,他說法語。他撈起腳邊銀幣,昂首走來,鞋跟一步步作響。那雙長靴踏壞了我的魔術陣,符文被拭成血跡。他目不斜視。在燭光下,他的眼睛是真正的金色,虹膜裡流有金屬色澤。身披白鼬皮草、品藍色的禮袍,金髮垂落肩胛,兩隻耳朵勾著鍍金耳飾、連帶身上勳章鏈與佩劍一齊叮叮噹噹搖晃。那些加總起來,也醒目不過他的太陽冠。
攤開掌中銀幣,他在我伸手欲接的同時抽回自己的指尖,執起我的,俯身吻進那隻慣用手,介居指關節與另一個指關節。皮手套之下,手背的令咒隱隱發癢。我看著他,一雙金色眼睛自睫毛後方昇起,他說:「見到您是朕的榮幸,我的御主。」
從他身上,我能嗅見教堂裡獨有的香脂氣息。
那個當口,我挪不開目光,猶如在等他幾可熔鑄聖杯的雙目煮沸我的。不明白為什麼。他是意料之外的類型,以英靈而言,尊貴的身份,過近的距離感。我想我不過一時之間不知作何回應。擔憂縮回手讓人感覺冒犯,考慮到他那身衣裝代表的涵義,我試著跟上他的禮節:「……敝姓海因里希。」我站定未動,不確定如何還禮,我的左手還落在他手中。「夏內・海因里希。」
「日耳曼的姓,法語的名字?」
「我是瑞士人。諒我法語說得不好。」
「相當謙虛。」他笑道。翻過手腕,另一手捧著,銀幣擱進我的掌心。「比起御主,我更樂於直呼戰友的名字,夏內。你願意的話也可以叫我路易。」
「我寧可不……。」我頓了頓,「讓敵手知道你是誰相當於自掀底牌。」
「放鬆點。我們還不在聖杯的所在地,對吧?」
「聖杯戰爭發生於義大利……半島,羅馬,如果你是想問。這裡接近阿爾卑斯。」
「我知道義大利。聖杯會確保我們能理解這個時代。」他掃視地窖拱頂,繞過我,端詳起牆上燭台,「你想怎麼過去?」
「搭瑞士航空?」
我本懷疑他真的能理解這句,誰料得到,他撥弄燭火的指尖轉而指向了我。
「告訴你的家僕,我要最好的位子。」
「你要佔一個機位?」
「為什麼不?我還從沒搭過飛機呢。」他又繞回來,一雙手按在了我的肩上,「作為我的御主,我也希望你了解,夏內,我的名號就是為了讓敵手知道而存在的。若非如此,所謂名號又有什麼意義可言呢?」
這就棘手了,我心想。
「你的名號可以自己留著,我不需要。」我挪開肩膀。看見他挑起眉了,不打算就此住嘴。「你是武器,要為我打贏戰爭。生鏽的劍就算威名赫赫也只進得了博物館,上不了戰場。你上過戰場嗎?」
「是御駕親征過幾次。」
我想也是。「殺過敵嗎?」
「……我是一國之君。」
「我想也是。我相信你還學過馬術。我有非贏不可的理由,需要我的從者和我覺悟相當。」我朝他示出那枚銀幣,「若非如此,你的名號便確實沒有意義。」
鏽蝕頭雕與他重合。他的視線並不落在幣上,「你此番言論,是因為你也還不確定我是誰,我說得對嗎?」他說。闔上了我的手。他錯了,但我不甘示弱。
「你說你叫路易,表示我還剩十八個選項。」
「那是好的開始。也許我叫查理會容易一點?」他笑著踱到一旁,找了靠牆的床坐下,雙腿交疊,做出「歡迎你坐在我旁邊」的手勢。我紋絲不動。
出乎意料地,我看見他蹙起眉頭,對我說,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他凝視我。那有本事帶給我一股錯覺,彷彿他在向我表示他需要我的認可。我上前一步,忍不住咂嘴。「召喚你是我父親的指示,我只想謹慎一點。」
「那麼這裡是貴府的地下室?看起來少說有百年歷史了。」他重整笑容,點了點床沿,「給僕人睡的?」
「那是給我睡的。」
我佇在那裡看他,以為他會打趣著說「你住在��穴?跟一隻蝙蝠一樣」或什麼。我倒寧願他有。他的表情變了,那較方才更加倍令我厭倦。他盯著我像是想說,但那件羊絨斗篷、蕾絲刺繡的襯衣……而實際上,他又不再接話,僅是起身,向拱門走去。
那張床彷如不曾存在。彷如我不曾睡在這裡。「我看不出——現在外面是幾點鐘?你吃過飯了嗎?」他連語氣也變了。一階一階步上,將門推開。
光湧了進來。我壓根睜不開眼。
・
ACT I.〈永恆之城〉
・
有時我能聽見遙遠的雨聲,或更準確地說,雨水打落在金屬、屋瓦、空盆栽那類東西之上,反彈出的聲音。有時我能回想出宅邸的全貌,猜測附近建材在雨中音量,雖說部份結構或許已在我無從得知的情況下被改建過,我不確定希留斯是不是會花時間翻新宅邸的那種人。我也能聽見雷聲,儘管看不見閃電。那裡唯一有光的一扇門,門縫光亮起的時間點,我猜是日落時分,若是,那就意味僅有到了夜晚,我才能看見一條細光滲出、映在通往門口的石階上。從光的輪廓我能猜測那盞燈大約離門不遠。然而我的意識還沒有清晰到,能夠記憶亮燈時長的變化,去猜測開燈的時機受不受日光節約影響。那裡空氣稀薄。也可能是戴著令我無法開口的面罩才導致我這麼以為。
有時會有人。分成定期巡邏跟檢查醫療器材的班次。他們的鞋影總把那條光切得像電碼,長短,長短,長。在門打開之前,我���能從腳步聲跟轉動鑰匙的聲音分辨兩個班次負責的人的不同,從不確定什麼時候開始,我的猜測從沒錯過,像家人分辨回來的是誰。那些人很少直接接觸我,穿得彷彿我是瘟疫,八成是為了避免他們身上魔力觸發我的防衛機制,讓我在不動手也不詠唱的情況下破壞掉拘束衣。
更小的時候,遠在母親離開以前,她帶我上過教堂。像最普通的家庭一般。就那麼幾次。地區的長老會,小禮拜堂,幾名孩童一道接受洗禮。同一時期,我也在希留斯的要求下開始認識世界的真實,從書與實踐中理解何謂魔術、魔法、神代,當然還有何謂根源。關於什麼和什麼大戰,什麼為了守護人類創造出了什麼,過去曾有許多神靈,真理就在世界外側,云云云云。再後來,我便不曾再見到母親。我猜,世界並非上帝歷時七天所創,同為魔術師的母親心知肚明,但是反正,是希留斯贏了,於是我成為了魔術師。
八歲那年的某日,希留斯把房門甩開。你能不經由基盤直接施術?他如是問。
我反應不及。他的聲音沉得很。你裝不了傻,我還記得他說,你不知道基盤是什麼意思?我保持鎮定。我說,我知道、我知道,基盤是世上刻有術式的學問或——這是抽考?我還在想他的第一句話,語意究竟是我做錯了,還是要我做得更多,就被扔進了地窖。
所以答案顯然是前者。起初希留斯的助理想靠魔術壓制,告訴我這是為了阻止我熔斷自己的魔術迴路,別抵抗才是上策,不久他們便發現帶魔力的枷鎖被破壞並非出於我的意願。諷刺的是,就結果看來,要拘禁一名魔術師,物理手段遠比魔術有效。
我住在那裡前後一共七年,今年十五歲,就連這件事,我都是出境時從護照上的出生跟辦理日期推算來的。相減得來的年數並不是成長,就像雨聲並不是雨,點燈不是日落,投影不是光,足音不是家人,記憶中父親母親說過的話也不是我住在那裡的原因本身。這一切因果都只是臆想。我常感覺自己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無所知。面對那些不曾讓我淋溼的雨聲如此,不曾得到他們任何解釋的父母如此。在那座不見天日的地窖裡,所有事物的輪廓都不過是某種感官資訊的殘遺,而我所知的也不過是事實本身投射出的皮影。真理跟陽光都在世界外側……希留斯這麼告訴過我。
至少在我召喚出太陽以前,希留斯曾是對的。
・
廣場上的市集人來人往。我和他對坐在街邊遮陽棚下。他翹著腳,冰淇淋紙碗空了,我還挖著已經半融了的那球巧克力榛果。義大利人就不會把椅子放在室內嗎,我瞇細眼,低聲碎嘴了一句,環顧四周,他突然雙手伸來,為我戴上原先掛在他領口的太陽眼鏡。我感到彆扭,因此遲了五秒才意識到最重要的問題何在。
「……這副太陽眼鏡是哪裡來的?」
「昨天,西班牙階梯附近。」他眨了眨眼,「記得嗎?你在咖啡廳店裡等外帶的時候,我發現隔壁——」
「什麼,紀念品店?」
「什麼?不是,我發現隔壁是Prada。」
我摘下眼鏡,瞥過鏡腳,又戴回去。
「……你該把皮夾還我了。」
「你打算每次買東西都跟我交接一次皮夾嗎?是你說由你付錢看起來不自然的。」
「那是因為你一直跟我走在一起!難道你不知道怎麼靈體化?」
「你不會說義大利語,總不希望一個人被當作跟父母走散,對吧?再說,你告訴我你擁有充足魔力,又要我保持靈體,這就像給我一張信用卡,卻叫我省著點花一樣。」他雙手環胸,說話時帶著演講般的手勢,說的卻滿嘴歪理。我長吁了口氣,撇過頭,撈起榛果醬裡的塑膠匙。黏的。我擱下,又比剛剛更不爽了。
他揚起眉笑。輪廓看上去和其他人類幾乎沒有區別。金髮在後腦繫成一束馬尾,叮噹作響的勳章全拿掉了,耳洞裡塞了耳釘,身上套著一件白色的絲質詩人襯衫。
遠處結伴的女性不時回頭瞧他。
只是一般遊客。我重新板起臉:「言歸正傳。我思考過了,要弄到一座城市的地下管線圖沒那麼容易,阻塞交通會比破壞自來水管簡單明瞭。羅馬到處都是古蹟,所以他們無法拓寬道路,平時路上已經夠壅塞,如果你破壞的是交通要道,比方說台伯河上的地鐵橋,就很難不引起注意。」
「……你聽起來像個亂臣賊子。」他愣了一下,像是沒有料到我會馬上切換話題。「你要我把橋斬成兩半嗎?」
「那麼你有不傷及無辜的個人原則嗎?」
他果真遲疑了。這副該死的太陽眼鏡八成讓他難以判斷我的表情是不是認真的,老實說,我有點得意。不過我的目的並不在此。
「沒事。我只需要一般人目擊不尋常的事件,讓教會頭痛。要是做到傷及無辜的程度,會有麻煩的反而是我們。」
他認真看我,想聽我說完。我考慮了那麽一秒是不是該出於禮貌拿掉眼鏡,讓他讀我。但我選擇把吃剩的冰淇淋推將過去。他接過紙碗,沒有猶豫地用了我的湯匙。我想他大概更在意自己的湯匙上是別的口味。
「魔術師相當重視隱匿神秘,因為神秘是越多人知道越會悖離本質的學問。當魔術越廣為人知,效力將會越低。魔術師只想把知識傳遞限縮在極少數人的範圍裡。事實上,這很弔詭,因為人類社會老早就背棄這種信條了。聖杯內建給你的後世知識包含啟蒙時代嗎?那個大名鼎鼎的伏爾泰可是你的頭號粉絲。」他仍默默地聽。所以他確實不會在咀嚼途中開口說話,我心想。「自啟蒙時代開始,一邊是權威,一邊是理性。隨著科學發展,人逐漸不再相信不可言說的奧妙,於是真理就從只有上帝知道的彼方,轉變成人們內心自有能力追求的此方。就我所知,那種思潮的影響在你的時代就已經有了端倪。」
「……什麼樣的?」他放下湯匙。「艾薩克・牛頓?伽利略?」
「是跟他們有點關係。我想說的是將自己的形象與太陽連結在一起有助於深植人心,但隨觀念改變,人們應該會需要你提出更具體的表達才對。」
他已經吃完了。不打算回應而已。
「擺脫曖昧的修辭,去理解真意,這被稱作除魅。人類社會就是靠著除魅走到現今,魔術師的社會卻與此背道而馳。我認為這就是魔術師的最大弱點,神秘這個詞彙的本質注定它只能走向消退、自取滅亡。
「教會也是同理。聖堂教會並不喜歡自家人以外的魔術師,這也是為什麼過去的聖杯戰爭,他們都被傳喚作為第三方進行監督,確保沒有哪名參戰魔術師會犯下出格的事。不過說穿了,教會的本質和其他魔術師沒什麼不同。像你這種不出自聖經的英靈,光天化日之下讓羅馬市民目擊神秘,無論監督者是誰都不可能坐視不管。」
「既然如此,隨意破壞哪個明顯的地標不會更容易嗎?」
「這座城市的地標全都是古蹟不是?我以為比起哪座髒亂的鐵橋,你會更不想傷到古蹟。」
他睜著那對金眼睛,停了片刻,從口袋掏出手機。
「這個怎麼樣?」
「……維托里亞諾,艾曼紐二世紀念堂?」
「建於二十世紀。」他竟一臉躍躍欲試。「重點是,上面說羅馬市民普遍認為它很礙眼。」
我抽出一張餐巾紙給他,決定不去問他的iPhone是從哪裡來的。
・
廣場距離維托里亞諾十來分鐘的路程。我們徒步沿艾曼紐二世大道過去,走在人行道石磚地上,身旁英靈的鞋跟聲總是響亮至極。他一面說話,一面分神於那些商店櫥窗:「要是教會的人真的找上門了,你打算怎麼做?」
「我只能打賭那個人不會想除掉我們,請他向監督者轉達我的來意。」
「要是他會呢?」
「那麽我的從者最好管用。」
「你該要有把握這行得通的。」
「你知道艾曼紐二世曾經被開除過教籍嗎?他統一義大利,連教宗國也不放過,教宗於是把自己囚禁在梵蒂岡城內。」轉頭一看,他正觀察著書報攤,「我們大可拿聖母大殿來開鍘。如果他們夠聰明,就該看出我們的誠意。」
「你想打賭教會足夠聰明?那風險可就大了。」
我失笑出聲。走了幾步,發現他還不跟上,正盯視著我。
「怎樣?」我問。
行人陸續繞過我們。
「……只是覺得你應該多笑點。以這個年紀的男孩而言,你太嚴肅了。」
語塞了一秒,也或許是三秒,我別開臉,兀自邁開步伐。「要挑釁教會還太早了?」我這麼說,心裡清楚他並非那個意思。
但這回換他笑了。「怎麼會。教宗派人向我賠罪的時候,我應該也只有二十初頭。」
人潮從紀念堂兩側解散,當中有人收起了手機照明。我繞行外牆,避開工作人員,這次轉而向後方透明電梯釋出魔力,熔斷電路彼端的保險絲,省卻再破壞一次備用電源的力氣。我們選定在建築側方會合。「頂樓的人走逃生梯下來會花點時間。」我瞥過錶,「大約五分鐘後行動。你確認得怎麼樣?」
「如果要斬斷柱廊,上面那座『自由的四馬雙輪戰車』位置很好。但搭電梯登頂可要十五歐元。」
好像他還在乎十五歐元似的。「反正你也只能從外面爬。還有問題嗎?」
在他身上早已是那襲禮袍,絲絨布上繡滿金色鳶尾,衣襬的鼬毛拖到了地上。他單膝跪下,「一起上去?」他問。拍了拍膝蓋,朝我張開手。
以大都會的標準而論,羅馬市街確實亂得可以。城牆因疆界變化而紛錯,古帝國的區劃技術在七丘間終究無可發揮,多神信仰的神廟、墓穴、古埃及方尖碑相依天主教堂,大道以廣場為中心放射,窄巷間立起殉道者像、神話人物的浮雕噴泉、法西斯政權紀念碑。來這裡幾天了,我沒有搞懂過這些建設規律,因為從沒有什麼規律。紅棕色、參差的天際線。整座城市生得像恐嚇信倒置拼回的一卷經文。
「大競技場在哪裡?我以為從這裡看得見。」
「大概在後方,另外一側。」我偏了偏頭,「我們從左邊的鮮花廣場過來的。」
「想繞去後面看看嗎?」
「……不用了。」
「沒事,別低頭看就行。」他將我摟緊。「這片十五歐元的風景如何?」
我斜眼看他,順帶瞟了眼右方,頂層確實無人,電梯也確實未在運轉。
「我倒是沒注意到市內哪裡都看得見維托里亞諾。但既然站在這裡能看見整個羅馬,這就說得通了。」
「你會喜歡的。絕佳的表演地點。」他說。望著市景微笑。大風吹動他的禮袍,絲絨上的鳶尾隨風沾過那身後四尊青銅馬。戰車像由展翅的維多利亞所馭。他同我佇立在塑像基座邊沿,整棟建築的至高點。白色屋頂正在我們腳下,橫亙紀念堂上層、白色柱廊兩側的白色山門上方。俯瞰整塊白色大理石砌成的維托里亞諾,那些浮雕看起來不過都像擠花。
天是陰的,柱廊之外沒有旅客。我們雙雙靜下。他的右手握好劍了。
我對上他的目光。
「你準備好了嗎?」
不確定是誰問的這句話。理應是我才對。但在我意識到自己因為失重感而背脊發涼之前,他早先將我整個人撈進了他的懷裡。來不及目睹他揮劍,那一刻,我被困在他的大袍之內,越過他的肩頭,逆風中睜開雙眼,視線所及既已是落石、粉塵、大大小小的浮雕像。那些羅馬柱的切口上鏡非常。櫥窗裡的瑞士捲般。空氣中四散的一切都是純白色的;有一瞬間,我甚至想不起現在應該是什麼季節。
也可能是我不曾意識季節已經有很長時間的緣故。我在彼刻,想起他推開那扇門。
拜日光所賜,地窖頭一次有時間感闖了進去。我睜不開眼,將臉埋於掌心。他走來,站到我面前,讓我站入他的陰影。他高大得根本不需要再穿那雙高跟鞋,我心想著,下意識攀住他的衣襬,透過指縫,看見他抬起手的影子始終停在半空。
他或許誤以為我在哭泣。
「在我身上有些狀況,應該先讓你了解。」我說。
他退一步。「你的眼睛?」
「這只是一般的生理機能退化……不,是我作為魔術師的體質並不尋常,問題從我八歲左右就被發現了。」我站直,撥去生理淚水。「我的魔術迴路能夠脫離基盤獨自運作,原因不明。我父親認為那是一種突變。」
「你——等等、等等,說得慢點。」他皺眉,停頓半晌。「好吧。所以那會有什麼影響?」
這得說到他懂為止。我吸了氣,「一般而言,魔術師體內的魔術迴路能夠將自己的生命力轉化為魔力,再將魔力傳送至基盤。你可以把基盤想成是一本無形的法典,裡面記載了術式的規則,魔術師便是靠著魔術迴路,以魔力連接基盤來發動世上現存的術式。我從很小開始修習魔術,到八歲時已經記得夠多術式,足以讓我的魔術迴路從已知演算出更多未知,過程全然跟基盤無關。」
「換句話說,你能自己發明魔術……?我已經看得出來你頭腦很好了。」
「不完全正確,這過程是更邏輯上的。就像得到兩條規則,兩者拼在一起得到第三條,第三條又和前兩……總之,不是憑空製造魔術,只是類推。我無法控制。魔術迴路的數量是天定的。雖然我的迴路生來就多於平均,往好處說,這表示我能提供你充足魔力,但再多終究是有限。迴路運作超出負載的那時,我就會死。」
他看著欲言又止,所以我靜下來等他。
「……是你父親為了這個將你關在這裡的,是嗎?」
「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嘆息,「這是為了保護他的繼承容器。魔術師家族都存在所謂的刻印,記錄有代代相傳的研究成果,藉由移植到繼承人身上來累積血脈素質。他認為我的迴路只要進化到某種程度,就很可能會排斥刻印移植。在他找到抑制的方法以前,我原本都該繼續住在這裡。」
「你被關押多久了?」
「老實說,我還不確定。被發現手上出現令咒不過是這幾天的事。我父親他只——」我和他對上了眼。「……我想說的是,要是不想使用魔術過度,我很可能就無法以魔術師身份幫上你什麼。我會盡可能避免,不過還是得提醒你,一個弄不好,我也有機會變成絆腳石,恕我無法接受我的從者不���謹慎。聖杯戰爭將是我的最後機會。就算逃過一死,一旦失敗我也得回到這裡。」
那就跟死幾乎是——我把那句也忍了下來。
後來,他當真得到了他的假護照,化名為路易・波旁。如他所願。他新購的衣物甚至一起塞進了我的行李。
與他走入登機門時正值秋季。
我開始聽見仿若雷鳴、一整道柱廊從中粉碎的聲音。
群眾驚叫。我瞪大雙眼,鑽出他的懷抱仰頭一看,他掃視腳下後明顯鬆了口氣。我順著望去,落塵漸漸散了,紀念堂上方、柱廊中央的部分業已塌成遺址。
沒事嗎,他回過神問,用不再持劍的那隻手撥正我的瀏海。我眨了下眼。沒事,沒有進沙,我說,撇去視線,鬆開了始終掖緊他衣角的指尖。
在他身上那股氣味,我想是沒藥,也可能包含薰燒過的乳香。
我們落地,站在正中央的無名烈士墓前。大理石階上沙塵遍佈。除了我們,這一側沒有半個人,人群全塞在對街的威尼斯廣場上遠觀。警察遲早會來,拉起封鎖線。近距離一看,我才稍遲地意識到自己的從者做了什麼好事——在我的指令下,他揮了一劍。就那麼一劍,足以讓整個羅馬看見這座城市的中心點、祖國的祭壇,變成一盤破碎的鮮奶油。而我甚至還懷疑過他的能耐。
這份力量不可能是他生前既有的,否則他就該自己帶兵出征了才對。但看看那些骨節分明的手指,別說因爲握劍而生繭了,他看起來像是活了一輩子,連自己的扣子都沒親手扣過幾顆。
十七世紀宮廷裡夜夜笙歌,堂堂一位國王,卻以Saber(劍士)的職階受召而來。
我看向他。
「夏內。」
我所召喚的從者唰地拔出了劍。
「現在,你想要我怎麼做?」
他昂首,眼神毫無戒懼,僅只是目視前方戴著眼鏡的神職人員步步走來。
彷彿他不介意來者再走得更近一些。
・
步下階梯,那神職人員敲了兩聲,推開教堂木門。他一手支在門扉上,「招待不周還請見諒。這裡平時只有舉辦婚禮才會使用,並不開放參觀,較便於談話。」近距離一看,他很可能只有三十歲,或者不到,髒金色頭髮梳得服貼,露出鬢邊的眼鏡鍊,羅馬領緊緊勒著。
「在宗座宮不便談話?」我隨口問。
「這我倒是無權代答,得直接請教主教閣下了。」
夠官僚,我心想。
所謂的主教閣下站在長椅走道盡頭,祭台前方,一雙手揹在身後,頭髮花白,看著不高,他穿的是紅袍。身後的門輕聲闔上。室內暗了,光從牆上的拱形窗透下。他轉過來,「噢,孩子,歡迎來到梵蒂岡。」他合掌,又展開雙臂,兩隻眼睛都是灰濁的,但不偏不倚朝我伸出了手。「羅倫佐・切拉里奧。很高興見到你。」
「羅馬教區代理主教?」我掃視他,然後握上去。「好個羅馬,監督者份量也不同尋常。」
「顯然你事先做過功課了。勤勉是好事。這幾天過得如何?永恆之城可跟你想像的一樣?現在十一月了,天氣是不穩一點。進入淡季,遊客應該會越來越少才是。」
「天氣很好,適合遛狗。」我虛應,回想了一遍義大利籍樞機的資料,但除了他的羅馬大學學位,什麼也想不起來。他們全是千篇一律的老男人。「站在高處連遠方都看得一清二楚。」
「啊——維托里亞諾,沒錯吧?伊澤基爾告訴我了。」他搖頭苦笑。
「戴眼鏡的神父?」
「他還只是執事,不過是的。是的,他轉達了你想和我見面的口信。我能知道你為什麼要那麼做嗎,孩子?為了讓我們出面找你?」
我緘默片刻,在他左手邊最前的長椅坐下,一腳斜伸出去,偏頭示意他坐——當然是右手邊另外一張。他面無慍色照辦了。「要知道這次聖杯戰爭的資訊,我相信問教會是最容易的。」我說。他側過身來,皺著眉。
「你說容易,是嗎?」
「解答一點疑惑不過是舉手之勞。反正在乎隱匿神秘的是你們,我沒有損失。」
「所以,你把在維托里亞諾的行動,當作是對教會的威脅。」
「還不是威脅,因此我會說是誠意。」
「在羅馬這裡,教廷的所在之處。」他雙手交握。「你天不怕地不怕。」
「怕——什麼?那個伊澤基爾是代行者?」
「教會裡並不存在代行者,那只是謠言罷了。」
「當然。任何事不留下證據就是謠言了。」
「你認為教會有此手段,但你不畏懼?」
手臂托在椅背上,我說:「聖杯戰爭的召喚儀式在羅馬境內發動,首當其衝的一定是聖堂教會。沒錯,這裡是羅馬,教會要暗中剷除參與者跟吹落葉一樣簡單。我這幾天牽著一隻醒目得不得了的英靈四處散步,你們有辦法動手,早就該動手了。」
「很莽撞。但不一定是壞事。」他笑道,帶著高齡者的聲沙。「我可以向你肯定,教宗閣下已經與坎特伯雷大主教閣下通過電話,英國時鐘塔方面,魔術協會的人士,希望教會承諾不介入這次羅馬的聖杯戰爭。當然,包括御主們的人身安全,也屬承諾範圍。教宗閣下非常看重這項任務,才會指名由我來承擔監督責任。」
他一開口就說得太多了。
「……是因為有御主出自時鐘塔?」
「在我回答你的問題以前,我想先了解,你非知道這些不可的理由是什麼呢?」
「贏得戰爭需要力量。人們說知識就是力量(power),您不同意嗎,主教閣下?」
「身為曾經的學院學者,老實告訴你,孩子,我更相信權力(power)就是知識。權力決定何謂知識。你同意我說的嗎?」
「你這麼說是在投其所好?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都這麼想?」
「我不會否認。作為本次聖杯戰爭的監督者,我也本來就想見你一面。」
「你是主教,而我十五歲——是這個意思?」
「你牽來的英靈就栓在外面,他的能力可不容小視。」他看起來反倒像是被逗樂了,「這也是我想與你見面最主要的原因。你是抽到Saber這張王牌的人,還年紀輕輕。實際說上話以後,我很高興知道你的膽識遠超過十五歲。」
「你何必需要我有膽識。」
「讓我們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吧。」他撐著椅背起身,不疾不徐走上讀經台。「首先,就我所知,這次聖杯戰爭的御主中,沒有人來自相同地區。而我們最早掌握來歷的御主,來自不列顛。她與時鐘塔並無干係,甚至很可能是所謂的外行人。她在本月五號,在節慶活動上,意外召喚出了一名Assassin(刺客)。」
「這個月五號?」我步離座位,雙臂環胸看他,「你說她是英格蘭人?」
「我認為就是你想的那麼回事。並且,我們尚未證實有哪名御主隸屬於時鐘塔。」
「可別說你透露這些是因為你拿勝負去簽了賭。」
「我能理解你的疑慮,孩子,我就開門見山說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次在羅馬發動聖杯召喚儀式的施術者,就是七名獲選御主其中一人。很不幸地,教會也還沒能把握所有御主的真實身份。以監督者的立場而言,最壞的情況,便是聖杯落入這名動機成謎的施術者手中。」
他一雙手撐在讀經台桌緣,瘦骨嶙峋的指頭點了又點。
「你想藉我除去心腹大患。」
「你並不信神,我說得沒錯嗎?」
「什麼?」
「你知道,過去我在神學院執教時,沒有遇過像你這樣雄辯的年輕人。我理解為,這是因為在學院、在聖堂教會裡,我們相信的是同樣的教條。我能看得出來,你和我們信仰者是不同的。告訴我,你想向聖杯許什麼樣的願望?」
我鬆開了肩膀,「……所有魔術師都會許的願望。我是聽令於家族來的。」
「那麼就是私欲。是凡人都有的束縛。」他把頭傾向另一邊,「在你聽來也許很諷刺,但研讀神學到這把年紀,說實話,現今社會,我更願意相信有著一己私欲的人,勝過能為信念赴死的人,因為你們有弱點。這名施術者,我認為他很可能並沒有。這麼龐大的行動,在聖座的眼皮底下,單純的私欲也許不足以作為動機。」
「你擔心這會演變成宗教戰爭?根據呢?」
「為什麼是羅馬?你認為對世人來說,這座城市代表著什麼?」
「教宗知道你打的算盤?」
「我認為教宗閣下,正是打定我會這麼處置,才選擇我擔任監督者的。」
我不說話,所以他又開口了。
「即便不相信我的理由,使那名施術者失去御主資格,也原本就是你的目標之一。你要聖杯,而我要的是守護羅馬。你有膽識,有聰明才智,最重要的是,你召喚出的英靈有強大的力量——看看維托里亞諾。假如真要簽賭,你絕對是我的不二人選。」
我側過臉,仰望拱形窗外,想起英靈閒談時說過,作為一個眾生都搶著美言的人出生反倒教他誰都不敢輕信,而那又讓他學會洞悉真心……諸如此類的。我想過那麼一秒把他叫進來,讓他發表高見,但蒙上帝恩典,他畢竟是「法國與納瓦爾最篤信基督的國王」。守護羅馬在我聽來像是屁話,在他聽來卻搞不好不是。
至少,有一件事切拉里奧說得千真萬確:我理解不了信仰者都在想些什麼。我是魔術師。這聽著矛盾,不過單就此情境,這跟「我是科學家」基本上是一樣意思。我看回切拉里奧,還有他身後那尊受難像。
「只要你同意合作,孩子,以示誠意,我會把教會掌握到的,關於本次聖杯召喚儀式的資訊都告知予你。」中立第三方的監督者是這麼說的。
・
「問題是,你相信他嗎?」
他遮住我的光了,我盯視地磚上翻著白眼的臉孔浮雕,心想。
「……這裡的地脈的確被動過手腳。陣法沿著貝尼尼兩道柱廊的範圍展開,從協和大道,這座方尖碑,一直到——」方尖碑另一側,聖伯多祿大殿的立面。隔著皮手套,掠過磚面文字,我站起身,「他找上我們的理由倒是挺合理的,你怎麼說?」
「主教閣下可以向我們揭露其他人,哪天也可以反過來出賣我們。」他聳肩。
「不過要是切拉里奧所說,關於聖杯召喚的細節是真的——我認為那不太可能由他憑空杜撰——至少我們對這名施術魔術師就不算是一無所知。」
「這不會是教會自己設的局嗎?我是說,在羅馬佈下這種東西……假如這個人真不屬於教會,那教會未免太無能了。」
聖伯多祿廣場上晴空萬里。上午的雲全都散了,西曬陽光穿過柱廊上矗立的聖人像列,刷亮了人群、圍欄。遠處的白鴿一哄而散。
「讓教會在羅馬挑起魔術大戰,就跟讓他們去研究大霹靂或是進化論一樣。其他地方也就算了,組織一旦龐大什麼人都會有,教會可以在任何地方自打嘴巴,就是不能在羅馬。」繞過方尖碑,我向大殿邁步。他跟上來。廣場群風將他的馬尾一綹一綹掀離背上。
「在我看來他們已經自打嘴巴了。聖伯多祿的繼承者,連自己的聖座都看管不好。」他說。
「聖伯多祿大殿、萬神殿、大競技場、古羅馬廣場,還有台伯河。切拉里奧說,這些靈地都被以投影魔術覆寫上了日本某座市鎮的地脈,用以供給聖杯魔力。那座市鎮在以前進行過不只一次聖杯戰爭。這在技術上是可行,動機卻根本說不通。」
「也許我們的施術者是從那裡來的。」
「也許。但只能解釋為什麼要投影那裡的地脈,不能解釋為什麼大費周章選擇羅馬。」
「你對那座市鎮了解多少?」
「你來過義大利嗎?」我止步階梯,前方是等待安檢進入教堂的隊伍尾列。一階之上,我轉過身去看他。
「什麼?不,派人傳遞口諭不算的話,沒有。當時的交通可不是鬧著玩的。」
「那麼你想進去看看嗎?」
「你是說,觀光?」
我點頭。
「這不像——」
「怎麼?」
「……很慷慨,我仁慈的御主。天父保佑。」
我們步入那些拱頂高窗投下的光。
(此處缺ㄌ一段,寫不出來)
希留斯從來不是一個好父親。
母親離開以後,宅邸裡的廂房大多是空著的。不必要的僕從都被希留斯辭去,唯獨我們二人和一位家政婦住在那裡。家政婦總是恪守規矩走僕人通道,家庭教師和希留斯的助理僅在工作時過來。多數時候,希留斯是我唯一會在宅邸裡說上話的人。
我已經記不清那位家政婦叫什麼名字。她年約四五十,身形豐滿,隨時都穿好一套白淨的連身工作衣。我們顯然不是什麼正常家庭。在阿爾卑斯山腳的城市,二十一世紀,不與人交際的一對父子住在封建時代般的大院之中,那位家政婦幹的又是為希留斯這樣的人打理家務的苦差事。她從未顯露出動搖的模樣。至少在我面前沒有。我記得她敲了門打斷希留斯的訓斥那個夜晚,她站在門口說:「海因里希先生,晚餐的燉菜已經好了。」面不改色,被希留斯打發著離開,彷彿毫不介意自己的雇主要為了一道煉金術的習練將誰扣留到多晚。
後來,我洗完澡,廚房的燈一盞也沒亮著。砂鍋鍋蓋像無人動過。走上二樓,我看見希留斯書房的門縫下有光,卻並未聽見銀器磕碰瓷盤的聲響。於是我回到廚房,一件一件數起櫥櫃裡的碗盤,確認了希留斯不多不少、著實只拿走他一人份的餐具。我給自己盛一盤冰涼的軟爛的菜,站在流理臺前快速吃完。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多數時候只意味著書房裡的一道背影。面窗,修著沒有人指望他修的指北針或者六分儀。在航海時代製造魔術禮裝曾是海因里希的家業。希留斯也許是個好兒子,我偶爾會這麼想。魔術師世家的弔詭之處也許就在於一個好兒子永遠當不成一個好的父親。
希留斯只在講授理論時變得多話。起初這曾讓我倍感新奇。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從不對父職表達不滿,然而亦不吝於讓我知道我是錯的。我失誤時,他可以滔滔不絕,甚至可以聽著非常殘忍;但在一百次的否定之後,假如我不再弄錯如何重現一面方解石的解理,他便會細唸幾聲「對」字,以低語般的音量,就像只想說給他自己聽。我得聚精會神才能不錯過他的一個「對」字。
關於知識,他有太多的見解。我是唯一在那座宅邸裡聽他傾吐的人。如此時光曾一直持續到他逐漸失去對我指出錯誤的空間為止,希留斯又隨著我年紀漸長而寡言了起來。
在那些指導裡頭,他說得最多的永遠是真理。他總會在言不及義、由我接上話頭之後,想起自己已經不是第一次談論同樣話題。「萬事萬物的本質,」語帶抑揚頓挫,他一向這麼開場,「柏拉圖稱之為理形,超越時空,如今只存在於世界外側,名為『根源』的起點。」那便是真理。和所有魔術師一樣,那是希留斯一生都想、也是他唯一想抵達的地方。
有時,看著希留斯示範操作時那張漠然的側臉,我會知道他人生在世最諷刺的,便是做了一輩子魔術研究,卻發現自己最大的成果,在於和一個聯姻來的平庸之輩生出了我這樣的異例。我是這個日薄西山家族裡未曾出現過的存在。他不以我為榮。即使有,那也是有條件的。我深諳這一點,因此從未認為過自己需要得到他的父愛。
希留斯對我說過最動聽的一席話,就只是告訴我,我是海因里希家通往根源的唯一希望。在我帶著令咒於地窖醒轉之時,他抓緊這隻左手如是說。他從來不是一個好父親。那是事實。但也許他當不成好父親,都是因為作為一名魔術師,沒有我,他就將什麼也不是。從小到大,我始終這麼說服自己。
・
從梵蒂岡回到特拉斯提弗列時已是黃昏。
我們設置為工房的兩層樓住宅位處巷弄,就在街區轉角。鐵捲門���方,一樓是棄置多年的老藥舖,窗框以木板封死,地毯爛得和地面幾乎融為一體,但收納藥材的抽屜櫃仍保持著乾燥,現改而存放煉金術用的物品。我把回程路上買的披薩三明治紙袋順手擱在前檯。我想先洗澡,我說,徑直上樓,聽見他從身後叫住我。
「你待會兒要喝點什麼嗎?」他拿起櫥櫃上的茶罐,朝我晃了晃。那是前天剛買的。我停在階梯半腰處,越過隔間看他,手指不由自主磨過扶手上的裂紋。
「……你會泡茶?」
他聳聳肩,「別這樣,我會學習。」又接著說:「我會Google。」
「那就紅茶。別打破任何東西就是了。」
我跨出兩三階,停下來說了一句,謝了。不等他對我笑,頭也不回走上二樓。
二樓臥房有兩面牆開了懸窗,一側面朝大街,浴室這頭對著小巷。闔上浴室窗外的百葉窗板,將西曬格擋在外,我拉起浴簾,扭開蓮蓬頭熱水。
與他抵達羅馬第一天時也是這樣的霧氣和白噪音。
抓著行李站在機場出口,近在眼前的雨聲讓我聽得入神,然後他叫了我的名字。我已經很久沒看過真正的雨,我回應。他便閉嘴了,握上行李箱提把另一側,直到我鬆手,重量落在他手裡,他看著我說,那是我們的計程車,在我向外張望時,報童帽按在了我的頭上。
我抓緊帽簷,快步上了車,不知怎麼地,不敢回頭看他。
嚴格說起來,藥鋪是他發現的。
中午放晴,我拿起手機在特拉斯提弗列兜轉,想辦法要弄到一間適合設下防護壁障的Airbnb。落腳觀光客喜歡的地方,方便隱身人群,避開空曠處。我折著手指,這麼對他說。短租。不要和其他房間相鄰。最好要有工作空間和現成傢俱。他在鏽蝕的鐵捲門上,噴漆和傳單殘膠之間看見那行電話號碼,小小的黑色字跡以法文寫著「僅租有誠者」。
雨頌太太在另一頭接起電話,當天從米蘭搭車來到羅馬。
我們在巷口的咖啡館等待。她看起來年約六十多歲,穿著米白色呢絨外套、碎花套裝,一見到我們便秀出一串舊鑰匙,比電話裡聽到的還要健談。「老實告訴你們,我也不知道他寫了招租。」扭開鑰匙前,她擦過門上的字跡,扶正眼鏡,對我們微笑,「我先生他過世很久了,我跟我兒子一家也已經不住羅馬很久,從沒接到過什麼租屋電話。所以我想也許這是命運,誰知道呢?」
「容我冒昧請教,您是義大利人,對嗎?」他站在一旁,傾身問。
「噢,是的。老頭子才是法國人,從尼斯來的。你們哪一個懂法文?」
「我是法國人,在巴黎長大。」他從義語改而答以一口做作的法語,笑容滿面和雨頌太太握手。「方才在店裡忘了自我介紹,請恕我失禮。我叫路易,路易・波旁,雨頌夫人,這孩子是夏內。我們其實都懂法文。夏內來自瑞士,他是……一個朋友的兒子,學校生活不太順利,我負責帶他來散心的。」
我瞪了他一眼,他仍面帶笑容不肯回頭。
「你們都有著法語的名字,太棒了。而你,路易,你甚至有著王室的名字���」
「我真希望我們還有王室,也許這樣八年級學習歷史的時候,其他孩子就不敢拿我的名字尋開心了。」
難以置信雨頌太太會被他的胡謅逗得開懷大笑,我挑眉看他,以嘴形復述:「你八年級的時候?」媽的,他讀懂我的唇語之後甚至笑得更樂了。
成為藥鋪學徒時,店長打理了二樓空房供雨頌先生暫居。那些臥室傢俱都由雨頌先生親製。他擅長工藝,又閒不下來,休息時也總埋首在臥室隔壁的倉儲間裡。店長千金,後來的雨頌太太告訴我們。
我把浴巾掛上胡桃木製的衣帽架。
走下樓,他在店舖後方的流理臺泡茶。「你要加糖嗎?冰塊呢?」他掂了掂我的馬克杯。我繞過他,打開一旁洗衣機,丟入換洗衣物,瞄了一眼他手中兩只杯子。
「……隨便,跟你一樣就行。」
舊式洗衣機的運轉聲很大。
打開披薩三明治紙盒,我不知道裡面裝著四個口味。我抬頭看他。他放下兩只杯子,慢條斯理拉開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你先選。想吃哪個?你吃辣嗎?我記得這個辣椒雞肉是今日特選之一。」
所以,我想起入住那晚,我們出門採購。需要新的床墊、衛生用品等等。他在賣場不斷停下來問我「電陶爐跟電磁爐有什麼不一樣」、「鵝絨被為什麼比鴨絨被還貴」。聽著Saber,我對他說,就算是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在精神上我就跟美國隊長一樣,差別是我只冰了七年。於是他又問:誰是美國隊長?
「……你可以自己Google。」輸入法切至法文,我把自己的手機扔給他。「歡迎來到2024年。」
他學得很快。真的很快。待我們的推車推到家飾區,他已經開始請Siri幫他搜尋茶杯材質。然後他拎起一對琺瑯杯,帶著笑意看我。我忍不住問:「為什麼要買兩個?你又不需要進食。」
他的表情彷彿我嘲笑了他的殘疾、他被深深冒犯到了似的。天地良心。
我把同一句話嚥了回去,拿了鷹嘴豆口味的。「……我一個人吃不了這麼多。」我改口說。
「你可以只吃一半,我們交換口味。」他挑了辣椒雞肉的那個。「我吃得完的。」
那天,我掏出信用卡時,轉頭看見他提著床墊組和購物袋,在櫃檯尾端等我。
紅茶喝起來有點太甜。
我搞不懂自己。要是他再問我一次,我大概還是會說隨便,跟你一樣就行。
・
翌日清早,外頭不到十五度。我多套了一件針織衫才扣上斗篷,和他步行至三分鐘路程內的咖啡館解決早餐。吃什麼通常由他決定,我沒太多意見,唯一有意見的是他跟著進食要花我雙倍預算,現在就連這點我好像也已經習以為常。咖啡館店面不大,時間尚早,列隊的人都在等候外帶。他到櫃檯點餐。我在飲料櫃旁找了個兩人座,拉開木椅。桌上報紙刊著維托里亞諾的滿版照片。
結婚蛋糕切開了!維托里亞諾毀於瓦斯氣爆,無人傷亡——標題如是寫。
我攤開頭版。
「……由於缺乏事發影像,結構工程師僅能推測,柱廊斷裂在同一位置可能與柱身拼接方式有關,類似景象也曾出現於古羅馬時代建築……。」
「……諷刺的是,為了興建維托里亞諾,許多卡比托利歐北側的遺跡在當時遭到移除,這座曾被許多羅馬市民認為『不夠古典』的新古典建築如今也走入了遺跡之列。由於建築外觀,維托里亞諾被反對者戲稱為『巨大的打字機』,又或是更為貼切的『結婚蛋糕』,正如它在這場事故中被切碎的模樣……。」
始作俑者端著托盤靠近。我把整份報紙扔到鄰桌,頭版朝下,偷睨了他一眼。
他將兩杯卡布奇諾、兩盤開心果抹醬的牛角麵包呈上桌面。「老闆他記得我們是第二次來,真是好記性。他問我們這幾天去了哪些景點,如果還沒去過維托里亞諾,那就為時已晚了。」
「我們壓線參觀了。」我應道。卡布奇諾還在冒煙。他失笑說沒錯,有幸見到她的最後一面。
褪去右手手套,我撕開麵包,嚐了一片。他隔著紙巾以三指拾起他的,張嘴咬下,稱不上小口,但他的吃相乾乾淨淨,抿了嘴唇,沒有沾到任何東西。他不說話。細嚼慢嚥。我這才發現他的嘴角生有梨渦;不在他笑的時候,而在他咀嚼的時候才第一次注意到。我看著他,心想那些酥皮碎屑一定非常美味,好像我並不是在吃和他一樣的麵包似的。
「怎麼了?」他抬頭看。
我的下唇還就著咖啡杯緣:「想問你這吃起來跟可頌有什麼不一樣。」
「我倒是沒吃過可頌。」他擱下麵包,捻過紙巾一角,以沒碰過任何東西的另一手端起咖啡。「但我吃過這個,牛角麵包(cornetto),對吧?還有咖啡。我還記得有人告訴我這來自威尼斯,咖啡從東方來,都是沒多少人嚐過的新發明。現在人們每天吃。但這吃起來比以前的有滋味多了。」
「你喜歡吃甜的?」
「我有嗎?」
我搖搖頭,「當我沒說。」他顯然有本錢習慣吃甜。
「你看到維托里亞諾的新聞了?」
「……剛剛看到報紙了。」他最好不要給我提什麼結婚蛋糕,我心想。
「那怎麼看都不是我們做的。」
「什麼?」
「威尼斯廣場。還有那尊雕像。」他啜了一口卡布奇諾,似乎在等我回應,但我也在等他說明。他恍然大悟:「……報紙上沒有,那一定發生在半夜。」
我掏出手機。
俯瞰威尼斯廣場,綠茵中有巨坑陷落,焦痕輻散了十數公尺。他熟練地按下暫停,雙擊快轉,「我很確定我們下樓的時候,這匹馬還五體健全。」他指著艾曼紐二世青銅像。塑像散落的部件上頭是筆直的穿心洞。此外,無名烈士墓缺了一角,紀念堂山門上的三角楣飾坑坑疤疤……我下令他動手時,我們的立足點就在那座山門之上。
第一直覺,我想到了切拉里奧,嫁禍或者掩蓋跡證的可能性,但他沒理由做得粗糙。這些缺損看著彷彿不是同一種方式製造出來的。
「你覺不覺得,」或者不是彷彿。「在我們離開後,這裡出現過不只一人?」
他和我對看一眼,「……但很難說。如果不是瓦斯事故,廣場上的坑就只可能是熱兵器做的,一個人使用多種熱兵器我想還不困難。只不過那些穿心洞是不是也有沾到硝煙,不去現場看看也沒法知道。」
「不,去了也意義不大。現在大概很難接近修復現場,夜晚行動又風險太高,不如直接問切拉里奧。讓你犧牲維托里亞諾就是為了這個。」
「那麼今天又要去找那位主教?」
「在那之前,還得先確認其他靈地是不是也如他所說,保險起見。教會要對聖伯多祿大殿略施小技太容易了。」
「古羅馬廣場、大競技場、萬神殿,離這裡最近的是哪一個?」
「都差不多,不過我猜是萬神殿,從這裡最快到右岸的路是走西斯托橋。你想先——」
「先吃完早餐吧。今天的行程會很滿的。」
他端起他的卡布奇諾和我碰杯。
0 notes
Text

一起看電影【日安同學漫畫】
曾有幾位讀者問我:「如何才能像你一樣塑造出這麼有靈魂的角色呢?像是黎朵、席波。」
首先真的很謝謝你們的肯定(感動哭) 塑造角色的方法有很多種,分享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方法:「遇到不同事情的時候,想像你的角色會如何反應。」例如我遇到強迫推銷,如果是黎朵遇到這件事,她會有什麼反應?我要出席一場正式的活動,換作是席波要參加,她會怎麼穿搭?
任何事情、任何情況都可以套用到你的角色身上,如此建立起一個個立體的事件,角色也就會鮮活起來。做這種想像的好處就是,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減少孤獨的感覺,感覺好像有人陪你一起面對。(怎麼越說越想哭?)
(附帶一提本篇漫畫中看的愛情電影是BG向)
角色/ #黎朵 #日安同學 #席波
#漫畫#原創#生活#日常#可愛#manga#drawing#taiwan#搞笑#comics#goodayclassmate#rihantongsyue#girls#lovely#original manga#watching movies#日安同學#黎朵#席波#看電影#女孩
13 notes
·
View notes
Text
少攀緣多唸經
以下一位有緣人分享,來文照登:
感覺最近整個大環境的氣場很不穩定,末學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耳朵處在耳鳴的狀態,為此曾請示精舍,開示結果是「地震」。這種地震前會出現耳鳴的現象,在醫學上被稱為「夏綠蒂現象」。最近耳鳴更加頻繁,有時頭還會出現悶痛,在地震頻傳的現在,也只能學會與耳鳴和平共處。而數週前,在夢中夢見開車與一台計程車擦撞,向精舍請示,是否暗示有車關?開示結果:「正確。三經108遍,專案化解車關」,感恩精舍此答案,解開我長期開車,總會出現心慌恐懼的疑慮,於是決定,在未完全化解車關之前,就盡量少開車。
可能氣場不穩的關係,發現周邊的人也容易出現情緒不穩的現象。上週四難得堂,本預計可以好好唸經,卻有人找我訴苦,在我這裡像鬼打牆一樣,重複相同的說辭,訴苦了2個多小時。幸好我平日有在唸《六祖壇經》,還能心平氣和接受情緒發洩,說幾句平靜她的話。但當離境來看這些世間事時,不禁感嘆世人真的把太多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面子問題」上。這在我們教育界老師如此,學生也如此,然後都認為自己是被傷害的人,久久在這個紛爭中無法轉念。
諸多事件下來,發現自己多少受到干擾,唸經沒有以前順暢,為了避免被影響,而對唸經產生退散心,逼自己要比平常多唸一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一來因為經文較長,唸一部要一個小時以上,以拉長自己唸經的時間,二來,《六祖壇經》對我的心靈,真的能產生安撫與安定的力量。通常唸到第二品之後,心就慢慢靜下來,感覺自己當下有「與世隔絕」的感覺,好像世間所有的煩惱、恐懼、害怕,都變得微不足道。
雖然因上班時間長,上班期間又有各種狀況,只剩下晚上幾個小時,是屬於自己的寶貴唸經時間,但幸好有《六祖壇經》的陪伴,讓我還可以心平氣和,度過這紛紛擾擾的不穩定期。每天就是唸到累了、想睡了,一覺天亮又是積極打拼的一天。現在的我,心害怕了,就唸《六祖壇經》,心茫然了,就唸《六祖壇��》,心六神無主了,就唸《六祖壇經》,經文的神奇力量就慢慢發生,或許這就是自性自度吧!
末學深知自己天性駑鈍,處亂世,就安靜沉潛唸經,少惹事攀緣,多向佛菩薩學習經中義理,期盼來世有個比今生更有智慧的心性與腦袋!感恩餘生能遇見精舍與佛法,指引末學一個處亂世之方,盡量持穩把日子過好就好!阿伯說過:「處逆境更要精進」。雖然不知道黎明何時來臨,但我深信,堅持終將必見璀璨陽光!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分享完畢)
夏綠蒂現象,是指有些人的耳石具有超導磁性,能與地震的頻率共鳴,因而提前感知地震即將來臨。這樣的個案在東西方都有,有些人甚至還能從耳鳴的頻率,判斷地震級數和大約位置。如同有緣人所述,最近整個大環境的氣場很不穩定,有些國家正在經歷冰火五重天,雷、電、冰、火、風,異常頻繁地出現,許多國家也飽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平民百姓的日子過得有點難過、艱辛,這些都不是危言聳聽,如果您常關心國際局勢,就會發現許多新聞都在說,甚至還有點含蓄。
其實,未來世界可能有個轉變,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舊有的磁場逐漸瓦解,新的磁場慢慢浮現,這是宇宙星體間能量磁場的轉換,是天文物理現象,所以影響宏大深遠。而如何平安地度過這個轉換?其實就是遵循天地運行的法則,依循天理,自得天地守護。
以下引用自淨空法師開示:「這個山整個崩下來,山上面那一層的樹木還在,當中的土突然崩塌下來,這從前沒見過的現象,沒見過。這在佛法講是什麼因?我們的心行不善感得大地鬆了,搖晃不定。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現在想想,有幾個人心在定中?心都不定,可以說是心慌意亂,現在社會一般大眾都是這樣的,沒有安全感。
從前人心是定的,他定在哪裡?定在倫理道德。因為以前教育,它從扎根教育就教這個,教你定在孝悌、定在五倫、定在五常、定在四維八德,一生起心動念、言語造作,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他都有個常規,他不越這個規,他心是定的。現在沒有了,現在心不定,沒有安全感,所以大地鬆了,大地也不定,這在大乘教裡講得通。
如果我們不能夠認真學習聖賢教誨,把心定下來,這個事情會常常發生,會愈來愈多,這麻煩大!防不勝防。你看這兩年地震的頻率比過去多得太多了,在整個世界來講,每個月都會有好幾次,不一定在哪個地方,頻率愈來愈多,災害愈來愈嚴重。
記住『一切法從心想生』,佛這句話說得太好!我們心想什麼?要常常想著祖宗的教誨,倫理道德,常常想著佛的教誨,佛叫我們『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把心定在極樂世界,把心定在阿彌陀佛。我們的心定了,山河大地也鞏固了,就不會出問題。所以,要定在發菩提心。
《禮記》裡面講,禮的精神是什麼?自卑而尊人,自己謙卑,尊重別人,這是禮,禮的根本。決定沒有貢高我慢,貢高我慢感應的是什麼?地震。我們就曉得,我們能夠自卑而尊人的話,我們居住這個地方不會發生地震。我們要相信佛,佛說的,不信就沒辦法,一定要相信,決定不懷疑,它就產生效果。」(引用結束)
誠如淨空法師所言,從大乘教義裡面來說,災難從哪來的?不善的心行,「一切法從心想生」,堅定的善心善願,我們居住的環境就變成堅實的大地,不會有災難、不會有地震、不會有土石流。持續地誦經、消業、行善、布施,我們就是定在佛菩薩的教導中,以此善心善願,不只冥陽兩利,還能守護天地。在這紛亂的世間,虔誠誦經就是在接引佛菩薩的高頻光明能量,來破迷除誤、平衡大地。
如同有緣人所述:「《六祖壇經》對我的心靈,真的能產生安撫與安定的力量。通常唸到第二品之後,心就慢慢靜下來,感覺自己當下有『與世隔絕』的感覺,好像世間所有的煩惱、恐懼、害怕,都變得微不足道。」小編自己也非常喜愛唸誦《六祖壇經》,經常經文唸著唸著就進入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從經文中吸收源源不絕的正能量,清洗、治癒、緩和、平靜。從經文中學習佛菩薩的智慧,內化成自己的心識,轉換為日常待人接物的習性,變得更平靜、祥和。
在大環境和身邊的人們都有許多波動的時刻,正如同有緣人所述:「幸好有《六祖壇經》的陪伴,讓我還可以心平氣和,度過這紛紛擾擾的不穩定期。每天就是唸到累了、想睡了,一覺天亮又是積極打拼的一天。現在的我,心害怕了,就唸《六祖壇經》,心茫然了,就唸《六祖壇經》、心六神無主了,就唸《六祖壇經》,經文的神奇力量就慢慢發生,或許這就是自性自度吧!」
您也能感受這種踏實祥和的寧靜,只要少攀緣、多唸經,外境的風風雨雨,自然與您擦身而過。若能內化經文,學習佛菩薩的智慧來立身處世,您也可以成為環境中的穩定力量,與佛攜手,一同前行。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韋馱菩薩
南無伽藍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摩訶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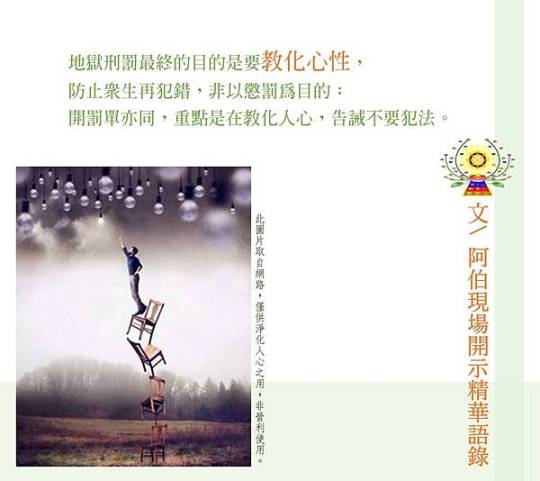
0 notes
Text
扫除日
2023年11月
“有一只野猫对自己的鼻子很感兴趣,正在满世界地寻找……”阿尔奇比亚德,旷土东北部的炼金师、药剂商人、生物学者、独腿老人正在一边背诵《传道法师列传》,一边打扫房间。屋外下着暴雨,他的侄孙正抱膝坐在角落,看向云雾弥漫的茂典阁,黎明之拱仍然安静地横亘在那上空。
论污垢的顽固程度,阁楼这扇三角形玻璃窗尤为突出。每天早上,老人都命令睡在此处的侄孙用魔法伎俩清理窗面,但自从上次庆典,疯法师的火球砸中了它,一些奇妙的裂痕出现了。孩子不肯放过观察这些裂痕的机会,久久地蹲伏在窗前,看破碎如棱镜般的街面。他甚至不惜偷窃姥爷的药水,用堪称不检点的方式调和,粘住玻璃边缘。实验事故败露的那天,阿尔奇比亚德一声长叹,捋了捋唇髭,抬起厚达两枚金币的珍禽异兽图鉴,给他的脑门来了一下。
现在,他正站在破损而粘腻的窗前,眯眼打量街道。依据咒法师、位面旅行者、他失踪已久的侄女尤弗哈斯之口,在遥远的被遗忘的国度,这个时节被称作枯萎之月。暴风雨打下了枝头的苹果,一个矮人铁匠窜到露台,收走了原本挂在那儿的围裙。忽然,他动了动耳朵,本就弯曲的脊背加倍拱了起来。
“怎么不念下去?阿尔奇比亚德,你不会忘了吧?”十岁的法师学徒啪地合上书本,投来质疑的眼神。
“急什么!”老人压低声音,“闭嘴,你难道听不见……”
“是药锅在冒泡,你有点神经过敏了。”
“笑话!我活了八十六年,还会被这点动静吓到?”
“说不定是客人呢。”法师学徒耸耸肩,踮起脚把书本复归原位。
“谁会在阿尔奇比亚德关店扫除的时候贸然来访?除非他情愿吃一记致病射线。有些人总爱尝尝苦头,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者不善。”
法师学徒沉默了,他不安地动了动,但眼神中还有一丝机警和期待。跳过堆叠的书山是一件难事,而对经验丰富的阅读者很简单。他两步窜到老人的断腿旁边,拽了拽被炼金药水腐蚀得破烂不堪的衣摆。
“……难道是鬼婆?我昨天又做了梦,还是那片林子,她呼唤我回归血统……”
阿尔奇比亚德睁大了眯缝眼,继而哈哈大笑,“只要你还在阿凯维沃一天,就犯不着担心那帮老东西抓走你。”他脸上的谨慎一扫而空,仿佛把危机感统统揉碎了扔进堕影冥界,换来滔滔不绝的絮叨,“比起这个诅咒,你不如担心担心血脉里的丧心病。瞧瞧这张蔫脸,这瘦弱的鸡爪,和你父亲一个样!我还记得勒菲弗尔氏拿到助手岗位前,发了疯似地捉狮鹫,野生的狮鹫……”
“我也想捉狮鹫。”学徒的眼睛突然光芒四射。
“那你就想吧!”阿尔奇比亚德呵斥道,“好了,快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师学徒熟练地往前躲了一步,防止被老人的独腿踹到屁股。他吐了吐舌,坐上了楼梯扶手,双手揣兜,借着重力和一颗懒惰的心,一路滑下楼去。
蹭着环形楼梯下降到一层的药剂铺,那种奇异的声音愈发清晰:就像在剪裁纸张,又像一双非人的小脚踩踏在沙地里。刚被列为一号嫌疑人的大锅里咕咚冒泡,一旁的菜板盛放着切碎的鼠尾草根茎,再然后是依据容量大小顺序排列的试管,旁边有一本被热气掀起、纸页忽上忽下的解剖书。
“奇怪?阿尔奇比亚德,你是不是——”
二号嫌疑人应声而动,门板上传来急促而疯狂的敲打声。
法师学徒怪叫一声,像只折了寿的老鼠,向后大跳一步,弓起了背,缩在桌脚下,再不吭声。
笃笃的下楼声没能掩盖住这突如其来的吵闹,雨水的潮味已然从门缝挤进室内,与药草的诡异熏香糅合在一起,对鼻腔形成张牙舞爪的态势。“该死的,一到雨天,义肢就会生锈……”阿尔奇比亚德发出恼怒的嘟囔,搀着断腿缓缓挪动,当他也来到这片区域,忽然打了个激灵,两只老眼瞪得浑圆,几乎把积年的眼翳都给撑开,然后,他像动物那样使劲嗅了嗅,略作一刻的沉默,爆发出了骇人的狂笑声。
“笑……么笑……”门缝里传来被暴雨冲刷着的微弱声音。
阿尔奇比亚德大步向前,穿行在他亲手搭建的三十平方米国土,没有理会桌下探出的两只充满好奇、但又瑟缩不前的眼睛。他轻车熟路地绕过宛如废品堆的材料架,像一具失能的死火山似地趴在地上,低声念叨了几句咒语。过了几秒,他才发出沙哑而得意的轻笑,缓缓站起,手中捏住了逃犯。
一声响亮的呱鸣撕开了空气。老炼金师满不在乎地扔掉手中物,同时做了一个轻快的手势。砰的一声,大门开启,一个发型夸张、长着硕大鼻子、身穿精美刺绣短衣的小个子毫无预料地摔了进来,以脸着地。
几乎是同一刻,完全符合阿尔奇比亚德预料的是,另一道身影从桌下猛窜出来,飞快地扑向了他刚才扔掉的活物——那是一只色泽鲜艳的钟角蛙。
“我为你感到不齿!”炼金师皱紧眉头,“要用魔法!”
“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啊!”侏儒从地上艰难爬起,“还以为你会迎接的是我呢,伯努瓦·勒菲弗尔!”
被喊到名字的法师学徒吃吃地笑起来,全神贯注地盯着闷在掌心的青蛙。阿尔奇比亚德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挥了挥手,一根靠在墙边的手杖飞向老人,他干脆用杖底勾起伯努瓦的后领,把他从地上揪起来。
“是你啊,跛鸭。”阿尔奇比亚德耸耸肩,把手杖平放在膝头,顺势陷进了一张软椅,“我还想谁这么不懂礼貌。暴雨天,关门清客的日子,也不提前写封信来,你就不怕我在地下室?这样谁能听见你的哀嚎?”
“哈!阿尔奇比亚德,臭老头!如果我不是认识了你二十年,又对这条街的风评相当熟悉,我甚至都会相信,你的字典里有‘礼貌’二字了。”侏儒替他小心地合上大门,踏着舞蹈般的步子上前,高举起短短的双手,“久别重逢!你的腰好些了吗?”
“呸!”伯努瓦打了个哆嗦,把舔进嘴巴的泥吐出来。钟角蛙惊恐而无助地看着他。
“糟透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我早就嘱咐好了他,如果哪天我突然死了,他要为每件器官找到用处。”阿尔奇比亚德憔悴地笑了,伸出手温柔地拥抱这位矮小的朋友,“跛鸭,多谢你四年前送来的药。”
“我如今带来了一份更好的礼物,你绝对意想不到。”侏儒眯起了眼睛,眼中闪动着狡黠的灵光,“虽然你不像制造金属爆炸时那样癫狂了,但脾气还是个倔老头,我相信你没放弃……”
“我可以拥有它吗?”伯努瓦双手捏着青蛙,打断了这位身高相仿的来客。
“当然,当然!拿去吧,小朋友!”跛鸭用上扬的声调说,露出了热情的微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噢,对,这只黏糊糊的朋友就是我在路上捡的,它落在一个小水坑里,我路过时靴子沾了水,简直要吓掉半条命,生怕把礼物给弄湿了!没错,我这次就是为了带来……”
“可以挖心吗?”伯努瓦又用两枚拇指掰动青蛙的胸腹,展示给跛鸭看。青蛙快速的眨眼就像在求救。
“……最好不要。当然啦,如果哪天它不幸身亡,譬如失足摔进了你们那口大锅,或者一个脚滑躺在了你姥爷的牙签上……反正,只要成了尸体,你当然可以身为朋友,替他处理一下身后事……咳,言归正传……”
忽然他停住了。因为,当他演讲时就会自然闭合的绿松石色大眼睛重新睁开时,跛鸭注意到,有一只小小的坩埚——显然是炼金师制造的人工生命仆从——飞舞在陷入沉思的伯努瓦和面露得意之色的阿尔奇比亚德之间,两只垂落的爪子紧攥着一封信件,正是从他兜里不翼而飞的那封。
“阿尔奇比亚德……!”跛鸭忿忿地咬牙,“我早该知道,你这老东西不会白白地给人拥抱!”
那个自命不凡的老头抬起了下巴,露出相当满意的微笑,他脸上的灰斑和褶皱都因此铺展开来,似乎真心实意地为这场恶作剧感到愉快。但在炫耀的言词流出口中之前,他的侄孙就伸出右手,一把将信件夺走了。微笑从他的老脸上转瞬即逝。
“是你不够经验丰富,跛鸭。等你活到八十六岁,身上就会神奇地长出名叫心眼的东西。”阿尔奇比亚德抢回信封,一把推开伯努瓦的脸,“没有落款?”
“没有落款。”跛鸭瞪了他一眼,脸上又复现出���和的表情,“你快拆开看吧。外面的雨下得可真大,我为了保护它,用皮带把它捆在肚脐眼上,用马甲遮着它,又用外套顶住斜前方的暴雨。这可不,我的靴子泡了脚,裤子都快掉下去,只有它还是干燥的、温暖的、留着墨水味儿的!我这身衣服还是从前那个行会老板的,俗话说,侏儒靠衣装,半人马靠鞍……”
伯努瓦的眼珠转了转,若有所思地瞧着那件沾满水珠的红外套。他想起阁楼的窗户并没有照出访客的身影,也许是碎裂的镜面起了作用,将这个本就瘦小的身形折叠得像只苹果。
“少废话。伯努瓦,拿裁信刀来。”老炼金师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侄孙,后者做了两遍手势,才不熟练地从远处取来一把刀,险些弄翻了路径上的一盆番红花。独腿老人嘀嘀咕咕地拆信,仿佛想抵御老朋友的唠叨,但在下一刻,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捂着门牙蔫蔫倒下。
然而,当他毫无痛觉地睁开眼,却发现眼前一无所变,粗粝舌头包裹的尖牙没有啃向他的鼻子,宝箱怪也没有给他一记老拳。只剩下些许魔法粉末,在光洁的信封表面淡淡发光。
“你暗算我,弗鲁格!如此粗鄙的恶作剧,连我十岁的侄孙都会做!”
“我没学过。”伯努瓦吃惊地说。
“闭嘴!”阿尔奇比亚德愤怒地揪住了自己的胡子。
绰号跛鸭、本名弗鲁格的侏儒幻术师叉着腰,爆发出一阵浑身舒爽的大笑。他脱下湿漉漉的外套,搭在一边,顺势跳上了炼金师面前的桌台,用矮小的身子为他们鞠上一躬,作了一个请的姿势。
阿尔奇比亚德恶狠狠地用鼻孔出气,一边用裁纸刀细致地沿线开封。伯努瓦在一旁啧啧称奇,即使是趁睡觉剪了他半边胡子的那天,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火气。信封里是一个牛皮纸包裹,牛皮纸里又是一只束口袋。跛鸭弗鲁格趁机把怀中的另一件礼物递给伯努瓦,那是一本《初级魔法学原理》,年幼的法师学徒瞪圆了眼睛,即刻欣喜若狂,把整张脸埋进书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纸浆的气味,露出陶醉的神情。
最后,出现在炼金师几乎腐坏的掌心的,是一片干瘪的树叶。透明密封袋阻止了他用熟稔的手法揉搓干叶,保持了它形状的完整。他莫测地瞅了一眼弗鲁格,后者心领神会,施施然开口。
“不久前,我梦见了古旅人。就是教授们曾经提到的那个庞然大物,有好多条手臂,古怪的眼睛,说着晦涩难懂的话。这些你都知道,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所以我跑回了斯翠海文,去翻巨龙们留下的藏品库。就在一阵乱翻中……我找到了她的痕迹,这不就想起你来了吗?”
“尤弗哈斯?”老人用鼻孔喷了口气,“我早把她给忘了。”
侏儒笑了笑,继续说道,“她当然不是一个圣法谕,那些混沌的研究没给她带来处罚都是万幸。况且,她跨越的是位面,而非时空。我想这两件事之间并无关联,梦境带来的启示是我将再次踏上旅程,但在临别之际,既然碰巧找到了你的家人的讯息,我这个老朋友怎能有所隐瞒?”
“论一心二用,没人赢得了你。”阿尔奇比亚德耸耸肩,看上去气消了大半。
伯努瓦把新书抱在胸前,有节奏地捏着青蛙的小脚。听到这里,他一把甩开手中的活物,扑到桌前仰视着侏儒,“弗鲁格!这片叶子是妈妈的研究?”
“想知道?那就摸摸看。”幻术师���屁股坐下,欢快地摇晃着两只灌了雨水的靴子,“包装这么多层,只是为了防范炼金师的急性子。万一当场揉碎了,我的法表里可没写修复术。”
阿尔奇比亚德闷哼一声,由着侄孙将密封袋夺走,而后小心翼翼地拆封。当枯叶落在他的掌心,便显现出真正的奥秘:它的外形平凡无奇,但对一片叶子来说着实太重。伯努瓦合并拇指与食指,用极轻的力道揉搓了一下叶片,其间的叶脉忽然映现出黯淡的光泽,仿佛通入电流。年幼的法师学徒张大嘴巴,恨不得一口将它吃下去;他那留着长长胡子的姥爷也不自觉地揉搓着双手,表露出一种近于纯真的喜悦。
“尤弗哈斯,是她的魔法微粒。”阿尔奇比亚德轻声感叹,“她还活着?”
“不一定。”弗鲁格出声反驳,又像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无情,尴尬地补充,“捐赠者是勒菲弗尔氏,所以,我想这是他们启程后的收藏品。别看这叶片长相寻常,它所起到的作用绝不只是拿来签名而已。老伙计,我知道你对魔法微粒的嗅觉敏感异常,一如从门缝里闻到了我。这份礼物,送得还算讨喜吧?”
炼金师不发一语地眯起那双促狭的、积攒着厚厚眼翳的老眼。法师学徒则直视着客人,点了点头,重新将其存入密封袋,珍惜地揣在怀里。
“那你呢,跛鸭?”阿尔奇比亚德反问道,“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弗鲁格一跃而起,拍了拍衬衫,神气十足地开了口,“现在就走。时光不等人,我的老朋友。要不是下定了决心,我又何必挑这样一个坏天气强行出门!”
“凭你的本事,我看是暴风雨娱乐了你。”
侏儒嘻嘻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他忽然露出怀念的表情,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老人。
“阿尔奇比亚德,我好想和你们再一次踏上旅程啊。”
“我也一样,弗鲁格。”老炼金师泰然自若地说,微微后仰,合上了眼睛。
尽管法师学徒对这段对话感到突兀和莫名其妙,另外两人却显然想起了什么。老炼金师摊出一只手掌,招呼对方靠近。侏儒幻术师耸耸肩,没有顾及前车之鉴,仍旧把胡桃木色的脑袋凑了过去。阿尔奇比亚德于是抬起了疲弱不堪的双臂,在这对窄小肩膀的两边都用力握了握。
借此机会,炼金师的人工生命仆从又将一种魔法物品挂在客人背后。那是一颗水滴状的细小物质,能够凭主人的心意吸收物品表面的水分,简而言之,就是能把暴雨淋湿的衣服迅速烘干。这动作轻巧得出奇,即使从法师学徒的视角能够看清一切,他也只是睁大了眼睛,怀着一种好玩的心态静静凝视。
只有当侏儒幻术师踏出门外,顺着旷土的漫漫长路独行远去,被巨大的启蒙火炬照亮时,也许会突然想挠个痒,继而发现这个迷你的饯别礼。
等到大门重新合上,暴雨倾轧的咆哮声骤然收束,余留下炼金药锅那温热而玄妙的气味。伯努瓦拍了拍手,抱着一刻也没有脱手的魔法书,踏着轻盈的步子,哼着小曲往阁楼上去,突然受到了一股向后的拉扯力,趔趄了半步。钟角蛙咕呱一声,从他的鞋尖险险跳过。
“还愣着干嘛?”阿尔奇比亚德板着老脸,放下手杖,“继续打扫。”
0 notes
Text
《她們的詩;她們的碎片》
<雲>
雲朵在天空中漫遊,
飛翔的希望騷動著,
反反覆覆。
白雲無法控制的生氣,
一場雷雨就突然來襲!
掃蕩過午後沉悶的心情,
追捕走煩悶不安的泥濘。
太陽接著撥開了憂愁,
耀眼的希望灑進了窗口。
——————
<歡唱的鳥兒>
老鼠在牆壁旁打洞,
小狗在草原上追逐,
貓咪在巷弄中穿梭,
鳥兒在樹枝間歡唱,
猴子在藤蔓外擺盪,
魚隻在河川內逆流,
海豚在洋流裡遨遊,
人類在世界裏模仿,
單純只是這樣而已。
——————
<漠外號角>
利刃劃破炙熱的號召,
寧靜的號角洶湧而來。
露水點在蘊紅的臂上,
殞落至地,
決心在矛盾的筆尖深思,
直抵黎明。
緋色殘影依舊不去,
駐足於雋永的沙漠。
廻響,
將止於一刻的永恆,
而利刃在我的倒影間,
雕下了狂熱足跡。
0 notes
Text
恋童的“萝莉岛”,到底有多脏?
最近,美国著名 " 爱泼斯坦案 " 名单浮出水面,长达 1200 页的密封文件被公开发布,引爆了热搜。
这个大淫魔的全名叫:杰弗里 · 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
他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做未成年人性交易,和他的名流朋友们一起,诱骗侵害未成年少女,而那份文件里则是有众多权贵名流,例如克林顿、安德鲁王子,甚至牵出霍金等人。
虽然文件提及了这些身处名流圈的人,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面临指控,也不能证明其有违法行为。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名单曝光后,居然有人说觉得那些被性侵的女孩很荣幸。
早在 2020 年,网飞就曾发布过纪录片《杰弗里 · 爱泼斯坦:肮脏的财富》。
里面采访了许多当年被侵害的少女,跟踪此案的警察、记者,回顾了臭名昭著的爱泼斯坦性交易罪恶,也揭露了 " 萝莉岛 " 的黑暗。
所谓的 " 萝莉岛 ",实际就是一个老男人打造出来的恋童癖岛。
打造恋童癖岛,他们到底有多脏?
受害者们口述的那些令人不适甚至窒息的故事,都是她们未成年时的亲身经历。
而制造这些罪恶的,就是杰弗里 · 爱泼斯坦。
一个靠学历造假上位的 investor,靠帮权贵打理资产,一步步打造出了自己的人脉网络成为神秘富豪。
他是个出生于美国的犹太人,高中毕业后进入库伯联盟学院就读,没毕业就退了学,后来就读于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研究所,但没有取得任何学位。
但在没有任何学历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够进入道尔顿学院当老师。
很快,他又带着教授的名号进入投资公司,很快成为合伙人,一步步混成了金融界的大佬。
杰弗里的财富怎么来的,很多人都只是猜测,只知道是帮富豪们打理资产,其他一无所知,但他到底有多富,看看豪宅就能猜个大概。
杰弗里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纽约、墨西哥、巴黎均拥有超级豪宅,坐拥好几架私人飞机,其中有一架是波音 747。
他还有一座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现在这个岛,有个别称:恋童癖之岛。长久以来,爱泼斯坦和他的名流朋友们,利用自己的金钱和权势,在世界各地的豪宅里,在小岛上,侵害了无数个未成年少女。
首先,参与性剥削的 " 名流权贵 " 们,一个个来头都不简单,政客、王室、金融大亨、娱乐大亨起步。
而在此次公开的文件中,不仅没有特朗普的名字,也证明了迈克尔杰克逊是清白的。
" 在公布的 170 多人涉案名单里,证明了被诬陷多年的迈克尔杰克逊是清白的,虽然 MJ 被证实和爱泼斯坦及受害者确实见过面,但没有去过他的萝莉岛,也拒绝了受害人的服务。"
而被剥削的未成年少女呢?都是年轻貌美的 "broken girls"。
爱泼斯坦和他的前女友希莱恩 · 麦克斯维尔,长期物色那些经济有困难、家庭有创伤的女孩,她们往往更需要 " 赚快钱 ",心灵也更脆弱,更容易操控。
对肮脏世界一无所知的少女们,天真地以为面前的大佬只是好心帮助她赚外快、见世面,抱着能去结交上层人物、出国留学、摆脱现实的期待,一步步沉沦。
爱泼斯坦以体面大佬身份,把女孩们骗到豪宅里,假借 " 按摩 " 的名义,要求双方脱掉衣服,然后在按摩期间实施性侵。
完事后,希莱恩 · 麦克斯维尔还告诉女孩们:" 按摩是你的福气 "。
这样的一次 " 按摩 ",他给女孩 200 美元,在那些豪宅里,一张张按摩床,仿佛恋童癖们犯罪的温床。
爱泼斯坦和前女友麦克斯维尔
而女孩们就像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刀俎,弱小到无法逃脱,被侵害了也不敢反抗。
一个上了小岛的女孩,试图从海上游走,结果却发现自己被 24 小时监控,迅速被带回。
爱泼斯坦有个专门的表单,记录了所有的女孩的信息,并且会标记出自己最喜欢的 " 按摩 " 女孩。
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随时随地,从不缺 " 按摩 "。
这些少女里,有一些表现乖巧顺从的女孩,会满足爱泼斯坦的各种性虐需求,接着就会被租用给其他的名流政客,成为名副其实的" 性奴隶 "。
还有一些性格比较硬又有贪念的女孩,不肯就范,会被爱泼斯坦发展成下线。
每介绍一个新的朋友可以获得赏金 200 美元,从而吞噬更多的少女加入其中,逼迫受害者站在 " 剥削者 " 的一方。
有的少女不仅自己被侵害,还拉了五六十个新的受害少女进狼窝,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活脱脱一个恋童传销组织。
肮脏名流们纵情释放着自己的人性之恶,而那些本就千疮百孔的女孩们,最终走向了自毁。
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曾经漂亮的女孩们,失去了容颜,变得苍老肥胖,他们有些吸毒上瘾,患上抑郁症、厌食症……
被性侵的耻辱一直萦绕,留下了抹不去的创伤。
" 我感觉自己脏了 "
" 在遇到爱泼斯坦之前,我是另一个样子 "
" 我感觉自己还是一朵正在绽放的花,但那之后,那朵花被连根拔起,被践踏碾碎。"
而那些发展过下线的女孩们,则在自责、愤怒、屈辱中惶惶度日,有的受害少女因为被媒体公布了私人照片和信息,工作被霸凌,遭受了无尽的诋毁。把坐牢当度假,
有权势就是为所欲为?
在被诱骗侵害的女孩们中,有两个最早站了出来。
1996 年,一个画家女孩和她未成年的妹妹被爱泼斯坦性侵后报案。
她们先举报给了警局,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又找到了《名利场》杂志。
负责的女记者被爱泼斯坦警告:" 要是我不喜欢这篇稿,你和你全家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不仅威胁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用好几个小猫的头颅恐吓了整个杂志社。
果不其然,最后这一篇报道,被杂志社改成了《有才的爱泼斯坦先生》,为他歌功颂德,丝毫没有提到两个受到伤害的女孩。
后来画家还一直遭到爱泼斯坦威胁,不断搬家,一直被恐吓。
直到 2005 年,更多的女孩报案,棕榈滩警局开始了长期的卧底调查。
他们调查了爱泼斯坦的员工,结果吃了闭门羹,一直追查,却总是被叫停,只好把案件移交给 FBI。
直到 2008 年,爱泼斯坦才因教唆未成年少女卖淫而被判罚 18 个月的 " 羁押与工作假释 "。
可怕的是,富豪的这一次入狱,坐监都像度假。
他住在监狱的私人区域,大门敞开,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随时会见律师,有专门服务他的警官,由爱泼斯坦付钱,时薪 42 美元 / 小时。
他一周 6 天可以在监狱外工作,每天外出工作 12 小时。
在监狱外,他可以让女孩们飞到办公室,继续发生性行为,监狱也就直接成了他的度假酒店。
在服刑 13 个月之后,爱泼斯坦获得假释,在假释期间,他无数次违规出行,四处飞豪宅,警方却拿他没办法。
在恋童癖罪行极恶的美国,贴着 " 性侵少女 " 标签的爱泼斯坦,人脉却丝毫没有被撼动。
获得缓刑之后,他第一时间开 party,请来了英国王子、伍迪艾伦等绝对大人物。
淫魔离奇死亡,案件就结束了?
2019 年 7 月 6 日,爱泼斯坦涉嫌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再次被联邦特工逮捕入狱。
这次他终于穿上了囚服,住进了最普通的牢房,所有的受害女孩和努力了数十年的警察们,终于有机会牵扯出这张巨大的卖淫网。
然而到了 8 月,审判还未开始,爱泼斯坦在狱中 " 自缢身亡 "。
一个关押公布缝制和大毒枭的联邦监狱,到处是摄像头和狱警,结果呢,狱警睡着了,摄像头也坏了,能出问题的地方全都出了问题。
而前女友麦克斯维尔则因协助诱拐未成年少女被判刑 20 年。
这一刻,所有名流们都松了一口气,纷纷和他撇清关系,迅速割席,忽然之间,所有人都跟爱泼斯坦不熟了。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说:" 我跟他不熟,我从来没去过恋童岛。"
根据警方搜出的航班记录,克林顿 2001~2003 年期间,一共有过 26 次乘坐爱泼斯坦私人飞机的记录,还有工作人员和女孩的人证,亲眼见到他在岛上。
英国王子安德鲁被女孩弗吉尼亚 · 罗伯茨实名指控,她 17 岁的时候被爱泼斯坦、安德鲁王子、哈佛教授性侵,并且遭受过性虐待,有一张合照为证。罗伯茨还说出了一个细节,那天的安德鲁,刚刚跳完舞全身都是汗地贴了过来。结果安德鲁王子闭眼否认三连:
" 我不认识她,不记得我有拍过这张照片 "。
" 我不记得我有去过二楼 "
" 我还有个罕见坏毛病,从不出汗 "。
真是 " 此地无银三百两 "、" 瞎话都不打草稿 " 的最佳代言人
这些疑点重重、前后矛盾的男人们,本该在爱泼斯坦被起诉后接受 FBI 的一同调查,等待一个个被打脸,接受法庭的判决。
结果随着杰弗里的死亡,所有人相安无事。
吊诡的是,一个资深法医申请对杰弗里进行尸检,发现他的舌骨三处断裂,自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显而易见,爱泼斯坦只不过是整个罪恶蜘蛛网里的一个螺丝钉,又或者是用完即弃的白手套。
罪恶没有得到法律惩戒,一个爱泼斯坦的死亡,背后还有无数个恋童恶魔在逍遥法外,这才是最细思恐极的地方。
她们的勇敢,
为烂透的世界带来一点光
这场牵扯到长达两个世纪的权、钱、色大案,随着爱泼斯坦的 " 自杀 " 后告一段落。
但如今 " 爱泼斯坦案 " 的文件再次被公开,而那些勇敢的女孩们,也应该重新被看见。
这些受到侵害的少女们长大了,很多都不再年轻,不再苗条,不再漂亮,有的回到了西班牙,有的远嫁澳大利亚,有的在受害者羞辱中一直堕落。
勇敢美丽的罗伯茨,她第一次指控安德鲁王子之后,遭受到了来自世界最大的恶意。
所有的指控被否认,她甚至还被报道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妓女。
曾经的她,遭受到性虐,被爱泼斯坦和女友要求生孩子,她设计逃到了泰国,和一个澳大利亚人结了婚,远走他乡,过上了普通的日子。
当爱泼斯坦被起诉,她选择再一次站了出来,揭开曾经的伤疤,再次面对世界的诋毁和中伤。
被恐吓了数十年的画家,重新拾起了画笔,她把所有的罪恶,都画了出来。
她还准备把那些勇敢的受害女孩,画成下一幅作品,鼓励更多人,要度过难关,大家需要互相支持。
这些女孩们,并不是 " 完美的受害者 "。
会因为堕过胎,被律师恶意提问:你堕过 3 次胎吗?被爱泼斯坦性侵和堕胎,哪个更糟糕?
来自恶魔、法庭和社会上的多重伤害,一次次把伤口撕开再撒上盐。
没人能跟她们共情,但她们彼此可以,在法庭外,面对长枪短炮的镜头,她们手挽手,互相安慰,彼此鼓励。
当不止一个受害者站出来的时候,其他受害者就有了力量。
" 当女性知道她们并不是人单势孤,就会更加勇敢地站出来。"
在爱泼斯坦案中有两位女法官也同样值得被记住。
一位是新泽西州的埃丝特 · 萨拉斯。
2020 年 7 月,有枪手闯入她家并枪击其丈夫和儿子,儿子最后不幸身亡,当时她正在地下室看爱泼斯坦相关的诉讼文件,于是才逃过一劫,而枪手是一名 " 反女权主义 " 的律师。
另一位是纽约曼哈顿联邦的洛雷塔 · 普雷斯卡,正是这位女法官做出裁决,解封了爱泼斯坦的档案。恋童岛就是恋童岛,整个事件也不是什么桃色秘闻。
这些未成年少女如同一张白纸,她们被恋童癖的人化作七情六欲的幻想对象,也总会被放到最危险的位置。
爱泼斯坦案中的恋童,他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病态的控制欲,更是拥有权力后对无力反抗的女性实施一种压迫,尽管过去一直有受害者在控诉,但他仍可以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从中获得快感。
而这些勇敢的女性受尽折磨还能重新来过,甚至在黑暗中为其余受害者带来了一丝光明,就足以值得所有人鼓掌。
0 notes